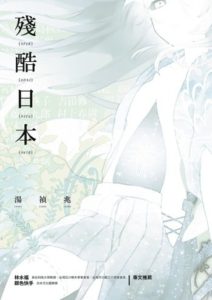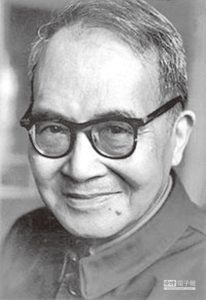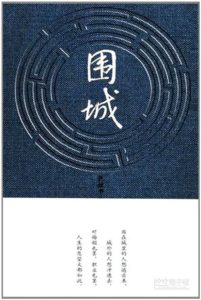歷史就是賓周
王德威
推薦書:馬家輝《龍頭鳳尾》(新經典文化出版)
《龍頭鳳尾》回顧香港淪陷一頁痛史
「賓周」是港粵俗語,指的是男性生殖器。這樣的詞彙粗鄙不文,卻是馬家輝小說《龍頭鳳尾》的當頭棒喝。這部小說敘述二次大戰香港淪陷始末,然而馬家輝進入歷史現場的方法著實令人吃驚。開始就寫敘事者馬家輝外祖父大啖牛賓周,以及江湖老大金盆洗撚,紅粉相好爭相握住他的那話兒深情道別。如果讀者覺得有礙觀瞻,好戲還在後頭。

《龍頭鳳尾》書影。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香港歷史如何與賓周發生關聯?《龍頭鳳尾》寫得葷腥不忌,堪稱近年香港文學異軍突起之作。作者馬家輝是香港文化名人,除了社會學教授本業外,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行有餘力,更從事專欄寫作。《龍頭鳳尾》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這個時代資訊如此輕薄快短,寫作長篇本身就是一種立場的宣誓,何況馬家輝有備而來:他要為香港寫下自己的見證。
馬家輝顯然認為香港歷史駁雜曲折,難以套用所謂「大河小說」或「史詩敘事」的公式;他也無意重拾後現代的牙慧,以顛覆戲弄為能事。香港是他生長於斯的所在,有太多不能已於言者的感情,必須用最獨特的方式來述說。《龍頭鳳尾》回顧香港淪陷一頁痛史,這段歷史卻被嵌入一個黑社會故事裡。主要人物不是男盜就是女娼,他們在亂世各憑本事,創造傳奇。但又有什麼傳奇比洪門堂口老大和殖民地英國情報官發展出一段傾城加斷背之戀更不可思議?
《龍頭鳳尾》書名典出牌九賭博的一種砌牌、發牌方法,由此馬家輝發展出層層隱喻:政治角力此起彼落,江湖鬥爭剛柔互剋,禁色之愛見首不見尾。命運的輪盤嘩嘩轉著,慾望的遊戲一開動就難以收拾,歷史的賭局從來不按牌理出牌。在一切吆五喝六的喧鬧後,一股寒涼之氣撲面而來。
馬家輝醞釀他的香港故事多年,一出手果然令人拍案驚奇。從殖民歷史到會黨祕辛、從革命反間到狹邪色情,他筆下的香港出落得複雜生猛,極陽剛也極陰柔。而在追蹤他筆下人物的冒險之際,我們要問《龍頭鳳尾》這樣的敘事有何脈絡可尋?什麼是馬家輝的香港鄉愁?尤其在香港前途紛紛擾擾的此刻,《龍頭鳳尾》這樣的小說又調動了什麼樣的想像,讓我們思考香港的前世今生?
男性之間政治與慾望的 糾纏角力才是香港本色
《龍頭鳳尾》的故事從1936年底發展到1943年春,這段時期香港經歷天翻地覆的變化。抗戰前夕香港已經是各種勢力的角逐所在,嶺南軍閥從陳濟棠到余漢謀莫不以此為退身之處,青幫洪門覬覦島上娼賭行業,英國殖民政權居高臨下,坐收漁利。抗戰爆發,香港局勢急轉直下,不僅難民蜂擁而至,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集團也在此展開鬥法。更重要的是英國殖民政權面臨日本帝國侵襲,危機一觸即發。
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突襲香港,英軍不堪一擊,只能做困獸之鬥。12月25日,日軍攻陷香港,殖民地總督楊慕琦代表英國在九龍半島酒店投降。香港成為日本占領區,磯谷廉介成為首任總督。以後的三年八個月香港歷經高壓統治,經濟民生備受摧殘。
七十多年以後馬家輝回顧這段香港史,想來深有感觸。但他處理的方式卻出人意表——「龍頭鳳尾」似乎也點出他的敘事策略。這就談到小說的主人公陸南才。陸出身廣東茂名河石鎮,本業木匠,除了手藝,身無長項。但命運的擺布由不得人,他離開家鄉,加入「南天王」陳濟棠的部隊,從此改變人生。軍隊生活只教會他吃喝嫖賭,終使他走投無路,只有偷渡香港。但誰能料到幾年之後,這個來自廣東鄉下的混混搖身一變,成為洪門「孫興社」的掌門人。
故事這才真正開始。馬家輝仔細敘述陸南才如何由拉洋車的苦力開始,一步一步和賭場、妓院,以及殖民勢力結緣,最後成為黑幫龍頭。然而龍頭的故事還有「鳳尾」的一半。原來陸南才側身賭場妓院,對聲色卻另有所鍾,他喜歡男人,而且是洋人。陸南才拉洋車時候邂逅殖民地情報官張迪臣,兩人關係從床上發展到床下。陸做了張的線民,張也回報以種種好處。陸成為「孫興社」老大,張自有他的功勞。
至此我們大致看出馬家輝處理《龍頭鳳尾》的脈絡。他一方面從江湖會黨的角度看待歷史轉折,一方面白描江湖、歷史之外的情山慾海。以往香港寫作的情色符號多以女性——尤其妓女——為主(如《蘇絲黃的世界》、《香港三部曲》)。馬家輝反其道而行,強調男性之間政治與慾望的糾纏角力才是香港本色。從情場、賭場到戰場,賓周的力量如此強硬,甚至排擠了女性在這本小說裡的位置。
馬家輝敘述陸南才的崛起,頗有傳統話本「發跡變泰」小說的趣味。紛紛亂世,英雄豪傑趁勢而起,幸與不幸,各憑天命。但馬家輝的故事帶有獨特的地域意義。陸南才的遭遇縱然奇特,卻不妨是上個世紀千百嶺南子弟的縮影。當他徒步五天從茂名南下深圳,穿越邊界,進入新界、九龍,終於抵達尖沙咀,那是生命的重新開始。
以淵源而論,陸南才的冒險其實更讓我們想起黃谷柳(1908-1977)四十年代的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蝦球傳》。蝦球出身貧民窟,十五歲離家跑江湖,雞鳴狗盜無所不為。他跟隨黑道卻屢被出賣,只有好心的妓女施予同情。蝦球歷經種種考驗,最後加入游擊隊,誓與惡勢力抗爭。《蝦球傳》每每被視為香港文學意識的轉折點。藉此黃谷柳寫出香港半下流社會的形形色色,也投射他對左翼革命憧憬。
相形之下,後革命時代的《龍頭鳳尾》不論寫陸南才傳奇或香港歷史興會就曖昧得多。馬家輝眼中的香港既是華夷共處的殖民地,也是龍蛇交雜的江湖。是在這樣的雙重視角下,香港的歷史舞台陡然放開。而當內地政爭延伸到香港時,情況更為詭譎。陸南才的出身猶如蝦球,但他周旋各種勢力之間,「力爭上游」;他沒有國家民族或階級革命的包袱,有的是盜亦有道的規矩。「皇帝由鬼子做,江湖卻依舊是我們的。」他做過英國人的耳目,也勉強聽命日本占領者。他參與杜月笙、戴笠的密謀,也主謀刺殺汪精衛親信林柏生的任務。馬家輝糅合歷史演義、會黨黑幕,狹邪情色等文類,雖未必能面面俱到,但善盡了說故事人的本分。他的港式土話粗話信手拈來,在在證明他是個「接地氣」的作家。
最令人矚目的是 陸、張的斷背之戀
《龍頭鳳尾》最令人矚目——或側目——的部分應是陸南才、張迪臣的斷背之戀。這兩人越過種族、階級、地域發展出一段宿命因緣,讀者可能覺得匪夷所思,馬家輝寫來卻一本正經。唯其如此,我們必須仔細思考他的動機。馬筆下的陸南才對同性的渴望其來有自,甚至還牽涉到少年創傷。藉著陸的屈辱與挫折,馬家輝意在寫出一種總也難以填滿的原慾,如何與歷史動力相互消長。
熱中後殖民理論讀者不難看出陸、張投射了百年香港華人和英國人之間愛恨交織的關係。這關係原是不對等的,甚至是一廂情願的,但假作真時真亦假,最終誰是主、誰是從,誰是龍、誰是鳳,難再分清。小說「龍」、「鳳」兩部分有著對位式權力交錯的安排,不是偶然。然而我認為馬家輝的用心有過於此。他更試圖藉陸、張的愛情描寫一種道德和政治的二律悖反關係。
擺盪在癡情和縱慾兩極之間,馬家輝如何完成他的香港敘事?他的二戰香港史是嬲的歷史,是嫐的歷史。小說高潮之一是陸南才為了張迪臣,在手臂上刺下「神」(粵語與「臣」同音)字以明志。用肉身「銘刻」愛情的歡喜悲傷,馬派浪漫,莫此為甚。
張愛玲的影響似乎不請自來
以上所論讓我們再次思考馬家輝面對香港今昔的立場和史觀。當香港從殖民時期過渡到特區時期,當「五十年不變」已由量變產生質變,新的危機時刻已然來臨。這些年馬家輝對香港公共事務就事論事,但作為小說作者,他選擇了更迂迴的——龍頭鳳尾的——方式來訴說自己的情懷。
我以為《龍頭鳳尾》之所以可讀,不僅是因為馬家輝以江湖、以愛慾為香港歷史編碼,更因為藉此他點出綿亙其下的「感覺結構」。那就是祕密和背叛。這兩個詞彙不斷出現,成為小說關鍵詞。在書裡,祕密是香港命運的黑箱作業,也是種種被有意無意遮蔽的倫理情境,或不可告人,或心照不宣,或居心叵測。相對於此,背叛就是對祕密的威脅和揭露,一場關於權力隱和顯、取和予的遊戲名稱。是在這層意義上,小說中陸南才、張迪臣的關係變得無比陰暗。
1941年香港淪陷是《龍頭鳳尾》情節的轉折點。在日軍砲火聲中,殖民地的繁華摧毀殆盡,而這也是陸南才和張迪臣兩人攤牌的時候。祕密一一揭穿,背叛就是宿命。剩下的只有傷害。戰火下的廢墟也成為陸南才心靈的寫照。
全香港的陷落彷彿只是驗證了陸南才個人的情殤。但是且慢,他的姿態讓我們想起了什麼?
我們還記得《傾城之戀》裡的范柳原、白流蘇在戰前香港游龍戲鳳,正是一對玩弄愛情祕密與背叛的高手。然而如張所言,那場葬送千萬人身家性命的戰爭成全了范、白。他們發現真情的可貴,從而完成傾城之戀。但在馬家輝的故事裡,香港淪陷只暴露了陸南才、張迪臣最後一點信任何其脆弱。當范柳原白流蘇在那堵文學史有名的牆下做出今生今世的盟誓時,陸南才展開他最後的背叛。男男版〈色.戒〉隱隱浮現。
家輝未必有意要與張愛玲對話,但祖師奶奶的影響似乎不請自來。藉著一個奇情的江湖故事,他回顧香港陸沉,並將感慨提升到抒情層次。
歷史的祕密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沒有真相,只見混沌。情義不再可恃,舉頭三尺但願有神明。多少年後,生存在此時此刻的香港,馬家輝猛然要發覺陸南才的感傷何曾須臾遠離。喧譁騷動之下,香港是憂鬱的。但又能如何?套用陸南才的粗口,是鳩但啦!
歷史就是賓周,亢奮有時,低迷有時。以猥褻寫悲哀,以狂想寫真實,香港故事無他,就是一場龍頭鳳尾的悲喜劇。天地玄黃,維多利亞港紅潮洶湧,作為小說家的馬家輝由過去望向未來,兀自為他的香港寫下性史——及心史。
(本文為刪節版)
聯副/書評/201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