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詩人比爾曼80嵗演唱會廖亦武受邀出席
2016年11月18日,家喻戶曉的柏林牆詩人兼歌手比爾曼,在
默克爾先生,洪堡大學化學教授致開幕詞,兩年前同樣的場景,是默
在演出之後的盛大酒會上,老廖我受仲維光老師之托,特地代表自己
我與默克爾交談了好一會兒,她笑嘻嘻說,還不會德語嗎?你回不去
攝影者:柏林文學節主席烏里



柏林牆詩人比爾曼80嵗演唱會廖亦武受邀出席
2016年11月18日,家喻戶曉的柏林牆詩人兼歌手比爾曼,在
默克爾先生,洪堡大學化學教授致開幕詞,兩年前同樣的場景,是默
在演出之後的盛大酒會上,老廖我受仲維光老師之托,特地代表自己
我與默克爾交談了好一會兒,她笑嘻嘻說,還不會德語嗎?你回不去
攝影者:柏林文學節主席烏里



有“禁书作家”之称的、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知名作家阎连科,日前在德国参加了长篇小说《受活》德文版巡回朗诵会。德国之声记者在杜塞尔多夫朗诵会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译成为德文的还很少。您是否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译为德文?如果有,是哪部?
阎连科:现在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和《受活》,都是Ulrich Kautz先生翻译的。第四部正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有可能,当然希望像法国、英国那样,一年一本,或者两年一本。比如现在正在翻译的是《四书》,《四书》后面是《炸裂志》,《日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多以农村和军队为主。您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想过写一部以城市为主题的作品。比如您的家也被强拆过,您会不会想到以”强拆”为主题来写一部作品?
阎连科:我想不太会,因为在中国,可写的故事要多得多,比”强拆”更复杂、更深刻,关于人性、人道,我想这样的故事多的很,非常多。我不会因为发生了一件强拆,就去写一个强拆。我每一部小说都要构思十年、十五年,甚至十七八年。很少出现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明天把它写成作品,这对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也不会用一种短篇或者中篇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值得写的比这个要多,而且要比它会好。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甚至有一个说法,说您是”禁书作家”。比如《四书》就没有办法在网上找到。您会对您的作品被禁感到很惋惜吗?或者说,您觉得,中国国内出版界的审查,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得到改变?
阎连科:《四书》可以在港台买得到,内陆没有出版。
关于”禁与不禁”,我一直在说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确实有个明确、也相对严格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如果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顺利的,没有被争论过的,我觉得这个作家是值得怀疑的。第二,被禁,也并不代表这个作品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作品被禁了,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讲清楚的。第三,审查制度短期不会像德国这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它一定会越来越严格。但是,这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碍。最大障碍当然是审查制度,还有自我审查,当然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的人格问题,怎么思考问题。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更重要。
(审查制度对中国社会)当然有影响,如果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乃至有一天,我们想象中民主、自由,人权那一天的到来,审查对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社会是有影响的。这是肯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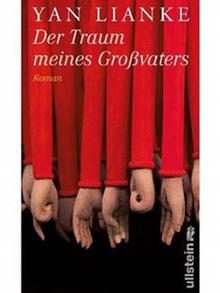
《丁庄梦》德文版封面
德国之声中文网:以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
阎连科:我和Kautz先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谈到的,”作家的独立人格”如何培育。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它有相当的包容性,并不是说你写了某一部不该写作的作品,就会像三十多年前,蹲监狱、杀头。现在社会甚至相当包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包容性。你写了,可以在香港、台湾出版,并不会影响我们。我指的是我们这个虚构小说,当然是为了艺术、为了文学,当然不是为了另外一种目的去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不能和”零八宪章”去相提并论。如果是为了艺术,你在香港、台湾出版,在德国出版,在其他地方出版,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如何解放自己,让自己的想象更加宽广,更加自由,这是所有作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今天一个作家的具体情况就是,我们面对权力也好,面对审查也好,更重要的是,面对金钱和权力,”名和利”,世俗的力量,有的时候超过了审查的历史。世俗对作家的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并不是说审查制度是我们写作的唯一障碍,”名利”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意思是,审查制度并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出好作品的唯一因素,而是说作家这个人,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阎连科:按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边是审查,一边又相当包容的情况下,我认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当然,三十多年前,我们不能这样去谈它。你写一部作品,蹲监狱、杀头,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就这样做。但是今天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文坛,您希望更多地看到怎样的作品?
阎连科: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都认为今天的文坛是1949年以后最好的一段时期。生态的环境、审查的制度,已经有许多问题,但是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无论如何都是相对顺利地写了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年。这是1949年以前,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的文坛,每一个作家都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非常丰富,非常复杂,非常荒诞,给作家提供了写不尽的文学资源,这是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的。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一部巨大的、伟大的、复杂的作品。当然,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写出来,有没有洞察力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写作的生态环境,在世界上一定是相对比较糟糕的,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故事的资源。我想这是两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在2009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没有办法写纪实的作品,您今天是否还是持这个观点呢?
阎连科:我经常说,在中国不要谈论纪实文学。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歌功颂德的不是纪实。中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也有许多好的、正面的、光亮的地方,写这种东西也是纪实,但是这种纪实应该交给媒体去做,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去完成的。我想,纪实一定是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是新闻报道无法完成的。我们的纪实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相比,我觉得不值一提,没什么可谈的。我们目前难以产生”非虚构”的作家。按她那样的思考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中国人、中国年轻人的阅读?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作品?
阎连科:他们不一定要读我们的作品,他们也可以读别的作品。只要是阅读,是文字的东西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成长。只要在阅读中,就一定会回到经典。这个比例是非常可观的。问题是今天的孩子,可能都停留在手机上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手机就不是一种阅读形式了。阅读,都是好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最喜欢的德语作品是什么?
阎连科:我还是更喜欢托马斯·曼的作品,另外《铁皮鼓》也很好。我们中国人还特别喜欢《香水》。中国作家对德国作品的阅读还是基本上停留在九十年代、两千年前后这一段。今天德国有很多好的小说,非常伟大的作品,比如Martin Walser,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形成阅读和出版,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鲍勃·迪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鲍勃·迪伦的歌词写得很好。以后我们中国的小品写的很好,你不能说它是戏剧,就给那些小品的作家一个戏剧奖吧。我想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中国小品是很好,有许多经典作品,经典的小品作家,这种人只要不拿诺贝尔奖,我觉得都可以。必须承认,他是了不得的歌手、文化人,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歌词当作文学去说,那未免两件事情。因为他的歌词离开他的嗓音,离开那个歌,作为诗歌,它是没有那么好的。他的歌词是必须让我们来听的,我们说的”文学”是让我们阅读的,这是本质的差别。当我们来阅读的时候,他是简单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也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国内目前只有莫言先生获奖。您怎么看待他获奖?您有没有期待您有一天也获奖?
阎连科:我想这都不是一个作家去想的问题。一个作家不要受任何影响,把你的作品写好,其他的事情交给命运去安排。你就把你的作品写好,这些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去安排,根本不要去想它。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我们回到他的作品上,我认为他是配得上诺贝尔奖的。其他的我们就不去谈了,他的作品还是很好的。
采访记者:简如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阎连科本人正如蒋方舟曾经对他的评价,“质朴、诚恳、狡黠、智慧、不清高、不装”。面对这样一个中等个头、微胖、说话甚至会害羞的中年人,很难想到他的身上贴满了各种极富争议性的标签: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中国最有潜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神实主义写作的创始人,等等。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挂职为“在职教师”的阎连科找到了他的新身份:文学教师。他现在将自己的时间平分,一半在北京,一半在香港;一半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学,一半回归作家本行。他说,从2015年开始,这一年以来在香港教书的时光会让他“从北京躁乱的环境中出来,重新去读书,去思考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写作。如果没有教书的过程,我不会特别系统地去想一些关于写作的问题”。
近日采访阎连科时,他刚刚来纽约第二天,是去领英国《金融时报》颁给他的奥本海默基金新兴之声奖 (FT/OppenheimerFunds Emerging Voices Awards)。而再过一天,他就要回到中国了。当时总统辩论进行到第二轮,阎连科诚实地评价道,自己因为语言不通,在电视上看到的也只是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表情而已。“但是有一点,无论谁来当这个总统,我们始终羡慕的是这个辩论的场景和相对的公正。”
他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四书》今年刚被翻译成英文,已于今年夏天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大跃进、大炼钢以及大饥荒的时代。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使用了极为挑战性的写作方式,如同书名所指,这本书分为四本“书”,来呼应《圣经》四大福音。这部企图重构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时人们遇到的种种生存绝境的小说在大陆未能出版。阎连科最为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等作品也大多遇到出版困境。
阎连科曾坦率地讲出中国文学的尴尬:在见证人性、历史、真相、空间、记忆时,中国文学无所作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作者面对这样“不敢写,自我阻挠”的困境时,阎连科又告诉我,审查制度对于他已经不再是创作上的阻碍,对于快到花甲之年的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写出来”。他本次采访中谈到了在香港教书、写中国以外的故事,以及对文革50周年的感想,访谈经过编辑与删减。
问:你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香港教写作课。能讲讲在香港教书对学生评价怎样?
答:香港理工大学要求我的班只能容纳三十多个人,但是每次都能来七十多个。香港的学生,而且都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文学的认识比我想像的要好。每个人每学期都需要写个短篇小说,字数不限,题材不限。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要讲出来,在班里一起讨论,他们都写得非常好,题材丰富,偏多一点的是校园题材,比如青春期的成长,还有些想不到的题材。他们会关注大陆、香港,他们会写到台湾,写到法国德国去。甚至还有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穿越小说、动物小说,当然,还有关于香港现实的小说,非常多元。
而且内地的出版社很愿意出版他们的小说,出一个香港大学生写的小说集,而内地的出版社对于中文的要求还是不算低的。这都是我们在内地的人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我根本没想过香港的孩子对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在他们之中,有没有人能够成为作家不重要。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问:那你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你感受到了怎样的秩序?从香港的大学生身上,你看到怎样的未来?
答:香港的学生几乎不会有迟到的。如果有迟到的,他/她会感到非常内疚,会表达歉意。但是我们的学生不太能表达出迟到后的内疚。我想这种对老师的尊重,对授课的尊重,都不太一样。香港的学生也很少有提前退场的。内地的学生,有时候,他/她不喜欢听的话就会扭头就走。还是蛮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从香港的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香港的未来不是学生能够决定的,是所有香港人决定的。我想,香港的未来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到的。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尊重那些学生们的独立性。我欣赏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独立性。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我有点歧视大陆学生,但是你必须承认他们的独立性是超过我们的。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我们学生对我们大陆民主的关注。
问:是不是因为香港学生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投票权,但是大陆学生就算再怎么关注,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无力感很强?
答:那也不一样,不能这样去讲。香港也不是一朝一夕变成这样的。对于大陆学生来说,即便你在微博微信上发些东西,也都是一种力量。我没有投票权,难道我就什么都不管吗?所有人不管,那么(一个目标)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正因为你走不到那一步,才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正因为无力,才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如果有力的话,几个人几个政策就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也就不需要(这样的参与)了。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每个人的关注。
问:中国对你的作品有重重审查,你有想过把你的文学的设定转移到海外吗?你经常写你的故乡河南,但你曾经说过好的文学是超越地域的文学,所以你想写写关于中国以外的故事吗?
答:我觉得(审查)和我没有关系,我内心的想像是自由的。它审查是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做到不自我审查。因为中国,你必须承认,它有很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写作是可以自由的。很多人没有独立精神,却老是怪罪审查。但是我们都不思考我们有没有独立精神。如果有的话,那是可以超越审查制度的。
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不仅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而且可能我也只能写那片土地(河南)上的故事。写作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最简单的规律就是,写作不能超越你熟悉的生活。你熟悉什么就写什么,你对哪个地方有情感,就有写作的冲动。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问:您是受文革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今年是文革50周年,毛泽东去世40周年,国内官方媒体集体噤声这件事,你是如何看待?那么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你又怎么看?
答:这就是中国的的复杂之处。既不能一味地讨论文革,也不能一味地讨论毛泽东怎样怎样。这是两个对立的问题。每一个讨论都有可能把中国推到另外一个方向。这正反映了中国在方向上的矛盾、纠结和犹豫。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表明,在一件事情上,中国可能在一个十字路口。既不能摆脱毛泽东,也不能彻底走向毛;既不能摆脱文革,也不能彻底走进文革去探讨。这是一个今年清晰的、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感觉,就是整个中国在未来方向上的犹豫。
对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我不清楚。但是非常多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有良知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表达的婉转又鲜明的态度,我有所感。比如在纪念文革多少多少周年的时候,很多网民与很多作者纪念老舍在1966年那年的自杀。很多自媒体在谈论老舍的死,那么由此能看出来,中国非常有良知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会推动和引导社会向前。
你不让我讨论中国,我可以讨论前苏联。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其实能看到在民间有股巨大的力量在牵制着一些非常上层的思想。你可能看到民间的巨大力量会推动社会往前走,无论多么缓慢,这个力量不会消退。你不让我谈文革,那么我可以谈老舍的死。借助老舍,通过解读老舍,去表达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这是远远大于纪念老舍本身的。每一个阅读的人都非常明白纪念老舍的弦外之音。
问:你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在重重审查的情况下。
答:因为年龄的原因,也因为我走过许多弯路,所以审查或是能不能出版已经不会影响我的写作了。我已经是朝着60岁走的人了,非常清晰我自己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对未来,我考虑能写出什么来,我想,写出来要远远比那些杞人忧天的考虑重要。写出来即便是不出版,即便没什么影响,即便一分钱稿费都不挣,写出来本身就是最最重要的。你在那里观望、犹豫,等生命慢慢消失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给我们的后人什么都没留下,那可能是更悲痛的事情。我不会想未来五年十年一百年是怎样的。我只在想今天在我的生命中应该把我思考的、我需要写的东西留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你现在的作品是怎样的进度?
答:我最新的小说应该会很快在美国出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很快上市,名字叫《炸裂志》。当然新近又出版了《日熄》,虽然在国内没出版,但在港台出版了。也拿了红楼梦奖(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立的文学奖,旨在表扬优秀华文长篇小说——编注),在国内出版也是遥遥无期。《日熄》明年也会接着开始翻译。这中间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应该会在明年出版。我想我的写作,在香港上课时,整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讲稿,整理完后,明年我会写新的长篇。这个长篇我基本上已经酝酿完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我会坐下来写作。这个长篇是宗教题材,关于所有中国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像是火车一样,来回行驶相相互互,不会交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它们没有什么交叉的地方。但是我希望它们在我的故事中交叉。在哪里交叉?我还在想。如何让这些人相遇?让他们之间发生一些文化的、宗教的碰撞?这是你的难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问:很多人评价你是中国下一个最有潜力拿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你怎么回应?
答:至于诺贝尔奖,这样的评论,就听听而已,笑笑而已。一个作家,要负责任,把小说写到最好。其他的都不是你要关心的事情。我只有责任把我的小说写好,其他的都要听从上天的安排。世界上比我优秀的作家多得是,世界上比中国文学伟大的文学也很多。每一个民族的文学的伟大都超出我们的预计。所以,你只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你会意识到你的作品是在世界文学中,是极小极小的,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点。
书评:禁不住的真實/Janice :文海 《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来源:香港明报周刊
 When I saw, leafing through a book about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these words on the copyright page the words “dedicated to Hong Kong as it holds on tightly to liberty amidst the wind and the rain”, I immediately wanted to read it. Living in Hong Kong, one still hears some news about how the director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get into trouble after their films are shown. In some places, whether a film is considered to be “independent” or not depends upon still depends upon the sources of its funding and the scale of the production. In China, “independent” means that the business world deliberately rejected it, the censor system opposes it and sometimes even the person safety of some people is at risk. In Hong Kong, where the storm clouds are getting thicker and darker with each passing day, are there people willing to evade eyes that would inspect and control their work, and seek the high moral ground of being a witness to history? Are they willing to disregard both the subtle and overt threats of those in power and as intellectuals, as Zeng Jinyan wrote in her preface call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When I saw, leafing through a book about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these words on the copyright page the words “dedicated to Hong Kong as it holds on tightly to liberty amidst the wind and the rain”, I immediately wanted to read it. Living in Hong Kong, one still hears some news about how the director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get into trouble after their films are shown. In some places, whether a film is considered to be “independent” or not depends upon still depends upon the sources of its funding and the scale of the production. In China, “independent” means that the business world deliberately rejected it, the censor system opposes it and sometimes even the person safety of some people is at risk. In Hong Kong, where the storm clouds are getting thicker and darker with each passing day, are there people willing to evade eyes that would inspect and control their work, and seek the high moral ground of being a witness to history? Are they willing to disregard both the subtle and overt threats of those in power and as intellectuals, as Zeng Jinyan wrote in her preface call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This book aims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values for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begins with what is seen in China as the taboo year of 1989. The book begins with not just what is in front of the lens but even more importantly with what lies behind the scenes to put into order the story of and reflections upon the ups and downs that face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these days. Directors pick up their video recorders, outline the dark side of the regime, and walk into the minefield to draw a map of the placement of the mines in the minefield. What they keep in mind is their dialogue with their audience, how they distribute their film, and how to continue their work. People working on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have had a great many experiences and discoveries in China that ar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root and decay that the regime is trying to hide. We can get a good idea of the methods they used to intervene from the thoughts and troubles of Chinese directors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o differences in style and attitude that distinguish one generation from another, the author in examining the phenomenon of post 1989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directly confronts the goal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Tempted by big markets and big profits, many people “in all kinds of organizations, quasi-organizations and circle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believing that they can hoodwink the censors, themselves in fact fall into the censors’ trap and, without realizing it, begin self-consciously filtering their own creative work, and imprisoning their own thinking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in an invisible iron lock box.” This i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that were mainstreamed without being even aware of it. Naturally some among them who are more sensitive and sharp witted. Director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who operate outside the system must piercing eyes and, going beyond the camera shots of a mere bystander, stride right into the eye of the storm and capture truths that are inaccessible to the people.
Some people question whether Chinese films that win prizes in foreign film exhibitions actually hav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merit. However, for those works that emerge after repeated repression, their aesthetic is in the quest of those people in them who are taking action. Just as Zeng Jinyan said, “Beauty is the respect people have for other human beings as human beings.” In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lms about the umbrella movement such as “Notes on a Troubled Time” are coming out one after another. Although these films are not shown in regular theaters they do find spaces where they are shown. Just in these spaces, the situation of independent films which come out in this chaotic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official system, needs to considered.

“The Gaze of Exile — The Testimony of China’s Independent Documentaries” by Wen Hai 文海 Publisher Qingxiang 倾向(Taiwan) Price: NT 399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Wen Hai, ancestral home Hunan Province, member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Wen Hai formerly made documentary films for Chinese Central Television which brought him in contact with people living on the lowest rungs of Chinese society. In 2000 he started to make films independently. His films include “The Story of a Military Training Camp”, “Uproar in the Dust” and “We”. He has interviewed Liu Xiabo and other dissidents. He wrote this book in 2013 – 2014 based on his work as a director and his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his book, Wen Hai testifies to how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served both to bear witness and as a tool of resistance since 1989.
偉大的加拿大創作歌手、音樂人、詩人與小說家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10日與世長辭,享壽82歲。他的臉書粉絲專頁貼出這個令舉世歌迷心碎的消息:
「我們滿懷哀慟在此宣布,傳奇詩人、歌曲創作人與藝術家李歐納.柯恩已經過世。我們失去音樂界一位最受敬重、最多產的前瞻者。之後我們將於洛杉磯舉行紀念儀式。柯恩家人哀悼之餘,期望世人能尊重他們的隱私。」
柯恩以淺斟低唱、沉鬱宛轉的嗓音風靡歌壇50年,歌詞中洋溢著對於宗教、政治、孤獨、性、人際關係的探討,名作如《Hallelujah》、《Suzanne》、《Bird on a Wire》、《Famous Blue Raincoat》都讓聽著低迴不已。在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舉世人心惶惶之際,傳來這樣的噩耗,分外令人悲傷。
今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巴布狄倫(Bob Dylan)曾形容柯恩的作品「深沉而真實」、「多面紛陳」、「具有驚人的旋律性」。巴布狄倫告訴《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人們談到柯恩時,經常忽略了他的旋律。對我而言,他的旋律與歌詞都是天才之作。」
柯恩從來不是所謂的「天王巨星」,也沒有拿過葛萊美獎(Grammy Award)但先後獲選進入加拿大音樂名人堂(Canadian Music Hall of Fame),加拿大創作名人堂(Canadian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美國搖滾名人堂(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同時被授予加拿大最高平民榮譽「加拿大勳章」 (Order of Canada)。
2008年柯恩獲選進入美國搖滾名人堂時,致辭人美國傳奇歌手路瑞德(Lou Reed)推崇他是「當今最高水平、最具影響力的歌曲創作人」(high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echelon of songwriters)。

1934年9月21日,柯恩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蒙特婁(Montreal)的威斯蒙(Westmount),一個雖屬中產階級、但源遠流長的猶太人家庭,母親一系來自立陶宛猶太世家,父親一系來自波蘭。柯恩曾說:「我從小就被人們耳提面命,我是亞倫(Aaron)的後裔。」亞倫是舊約聖經中的先知,摩西(Moses)的兄長,古以色列人第一位大祭司(High Priest)。
柯恩曾經戲稱,他的第一志願其實是當詩人,但實在無法養家活口,所以才改行當歌手。但是他剛出道時非常害羞,曾經唱紅《Suzanne》的美國女歌手茱蒂柯林斯(Judy Collins)回憶, 柯恩第一次登台時,唱到半場居然開溜,她百般哄騙才讓他回到舞台。
1960年代,美國民歌復興,柯恩與巴布狄倫、瓊妮米契兒(Joni Mitchell)、瓊拜雅(Joan Baez)、茱蒂柯林斯都是一時俊彥,經常一起巡迴演唱,後來雖然風格稍稍趨向流行,但詞曲創作仍維持鮮明的個人風格,嗓音也越發沙啞深沉。
美國鄉村歌手、影星克利斯克里斯多佛森(Kris Kristofferson)曾說,他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鐫刻柯恩《Bird on a Wire》的第一段歌詞。但其實這段歌詞,柯恩本人或許也會考慮留給自己當墓誌銘:
「像一隻佇立在電線上的鳥兒,像一個午夜合唱團的醉鬼,我以自己的方式爭取自由。」
“Like a bird on a wire, like a drunk in a midnight choir, I have tried in my way to be free.”
從歌詞到旋律,柯恩的作品總帶有一股陰鬱的氣質,但往往以黑色幽默點綴其間。他一生經歷多次憂鬱症發作,也曾沾染酒精與毒品,有記者問他是不是個悲觀主義者,他回答:「我完全不認為自己是悲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會一直等待下雨,但我早已全身濕透。」

今年稍早,柯恩接受《紐約客》專訪,談到死亡,「我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希望過程不會太不舒服。」1970年代之後,柯恩對佛教涉獵日深,成為日本旅美禪宗大師佐佐木承周的門徒。
20多張專輯之外,柯恩還留下10多部詩集與小說。上個月21日,柯恩發表60年歌唱生涯第14張錄音室專輯《You Want It Darker》,依舊好評如潮,但卻是他的天鵝之歌。
来源:风传媒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除讓大家都跌破眼鏡外,幾乎每個國家領袖都因美國是強國,而不敢不從,並且給予行禮如儀的祝福,不敢得罪美國老大。政治現實如此,但是身為世界公民的每個人都要吞下這錯誤的價值觀嗎?美國是全世界武力最強盛、號稱民主根深柢固的國家,因為川普的仇視言論,美國近日發生的社會仇恨與族群對立升高,許多在美國的非白人遭到各種騷擾與威脅,已經讓人擔憂,美國還是一個講究人權的民主國家嗎?
美國一直都存有種族歧視的問題,一直也都沒有真正做過轉型正義。有人認為,美國有良好的機制,可以抵制非法的仇視言論與行為,但是社會對立已造成,仇恨已散播在人心,深感被侵犯、壓迫的非白人、女性及穆斯林族群將如何自處?這些人也擔任國家公職,擔任社會上各階層的工作,現在白人基督徒自以為出頭了,到底會在美國造成怎樣的社會傷害?白人還會尊敬執勤的非白人警察嗎?黑人的將官士兵還會真心效忠貶損自己的領袖嗎?穆斯林女人害怕戴頭罩被侵擾,可是她們又做錯什麼?
川普勝選以後,歐巴馬和川普如同以往所有的政客展現風度,和好言歡,但是人民久未被處理及認清的仇視敵對異類與白人、男人優越感的心態,都讓歧視者找到沃土,不論學校與民間仇視者找到了生根的角落,他們肆無忌憚地用言語、暴行,侮蔑他們所有心中仇視的對象,他們不必再遮掩,不必擔心犯法,因為川普是總統了,他就是「最好」的示範。
德國因為種族歧視犯下大錯,至今憲法基本法第一條第一款條文昭示,「人類尊嚴,不容侵犯」。所有紀念碑與過去的納粹集中營,都還矗立在德國。很多人不想看,也不可能忽視媒體報導的紀念日而睜眼說瞎話。德國的紀念作為,並不是僅為德國,其實更是要給全世界人警示。
選舉中商場的推銷言語,變為日常仇視的言語,為了勝選而不擇手段踐踏別人尊嚴的川普,已成功擊毀人類長期以來爭取的人人平等之普世價值。美國擁有大片領土,國力強盛,但並非什麼都是健全的。美國在國境外當世界警察久了,想要退回內政,可以理解。但在國內的內政上,川普卻使用了強烈的族群分裂手段。
當選後,他一本正經地說,他愛美國,但是要團結的第一步,就是要先認錯,才能讓被傷害者原諒,傷口才有重生的機會。如果他有領導智慧,看到美國現在社會上人民的仇恨劇升,相對弱勢的害怕與恐懼,應該要馬上出來真誠認錯,才能彌補他所侵犯的人性尊嚴。否則,美國要因為他而偉大之前,將會先因為他而毀滅。
每個當選者,都應該有機會給予祝福與領導的機會。但是當選者成為領導者時,一定要有認錯的能力,不然就像希特勒領導的種族歧視之政權,仇視異類化為極致後,走到窮途末路,帶著國家毀滅,最後舉槍自盡,帶給國家民族的罪孽,更是禍延子孫,全世界公民能夠不深思嗎?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来源:自由电子时报

独立中文笔会创立15周年,在台北举行纪念会,
由中国流亡作家贝岭以及诗人孟浪所创设的独立中文笔会,
贝岭指出:“独立中文笔会今年15周年的庆祝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林昭纪念奖”由著有《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
孟浪表示,
流亡作家王一梁朗诵“孟浪和我与《自由写作》”主题发言,他说,
适逢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民海“被失踪”事件一年之际,
他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戕害出版自由,并呼吁中国公开审判,
八九民运人士吾尔开希也应邀与会,他则强调“独立”是一个了不起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 台北报导 (责编:黄春梅)

中国诗人王藏(资料图片)
自由写作奖的颁奖词中写道:“王藏的文学写作,尤其是他的诗歌成就,证明作为个体在面对专制的野蛮和颟顸时,所迸发出的强大词语能量……王藏作为80后一代人,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他在诗歌中带给我们心灵上和感官上的冲击力度,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汉语表现的宽广空间。”

吾尔开希等人士赶来支持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获奖感受
对于未能亲自前往台湾领奖,王藏称,自己孩子还小,暂时走不开,并且认为当局可能不会为其办理出境手续。他对美国之音谈了获奖感受。
王藏:我在得知获奖之后,写了一篇获奖致辞,作为独立写作者,就必须面对我们身处的集权社会的现实,要面对苦难,要突出我们对社会的真实看法。我诗歌所表达的对自由的追求、对集权的反抗,我不能光停留在语言上,我认为还要具体的行动。这样我觉得活着才有一些意义。后来对香港占中声援,参与行为艺术,这些都是延续我诗行合一的人生理念。我知道获得这个奖的前12届都是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老师,各方面都有很大成就。我个人认为与历届获得者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我是一个80后,我的写作之路还很漫长。把这个奖颁给我,我认为是一种鼓励。鼓励大于写作成绩的认可。
言论受压制时代的诗人
出生于1985年的王藏,2003年开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王藏称,当时大学尚未毕业,即受到学校和国保压力,甚至以不发毕业证相威胁。王藏认为,近几年言论空间大为缩水。
王藏: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氛围更加糟糕,很多被判刑的、被黑监狱的、被人权迫害的,明显比江泽民、胡锦涛那个时候更为严峻。已经是在朝鲜的路上。国家公开用法律的方式耍流氓。用法律去治人。中国不存在法制,只存在用法律的外套,这种口袋,去收拾一切异见分子,一切威胁到他意识形态,威胁到他维稳的一切,都用寻衅滋事、煽颠、各种罪名,各种口袋罪,把所有反对的声音全部消灭。
谈及家庭,王藏表示了自己的愧疚。
王藏: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理解支持我所做的事情。我内心感受到的压力是我关注这些事情,我不能在体制内获得工作,不能带来经济上更好的收入。我们在经济上一直勉强应付,这是我唯一对家人的愧疚。

王藏妻子王丽和女儿 (推特图片)
王藏作为以“人本思想”为基础、走向底层社会的“低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作主题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评论家认为其作品为“诗化论政”,评价这位先锋诗人具有诗行合一的艺术魅力和担当精神。其主要作品包括《小王子语录》(短诗集)、《故园 黑砖窑》(诗集)、《血色格桑花》(诗集)、《没有墓碑的墓志铭》(长诗)。
2012年,王藏入住独立艺术家群体聚居的北京宋庄艺术村,在创作的同时参与维权活动。2014年10月香港“占中”雨伞运动期间,王藏在网络上发布撑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占中”,其后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将其拘留。2015年7月,北京通州区检察院决定对王藏不予起诉而释放。王藏在北京期间,因受到国保压力,多次被迫搬家。
据介绍,独立中文笔会自2002年起创设一年一度的自由写作奖。2016年度该奖项奖金为3000美元。王藏获奖前,自由写作奖已有12届获奖者,分别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廖亦武、周勍、汪建辉、野夫、杨显惠、卢跃刚、陈子明、杨继绳。
来源:美国之音

吾尔开希等人士赶来支持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独立中文笔会近日在台北的国际艺术村宝藏岩纪念创会15周年,并举行一系列活动,以现场探讨和远程参与的方式与全世界公民记者与专家共同探讨网络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发展。
独立中文笔会于2016年10月26日至30日在台北举行独立书店纪录片制作自媒体创设技术工作坊,并纪念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此次笔会将2016年度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予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自由写作奖得主为中国80后诗人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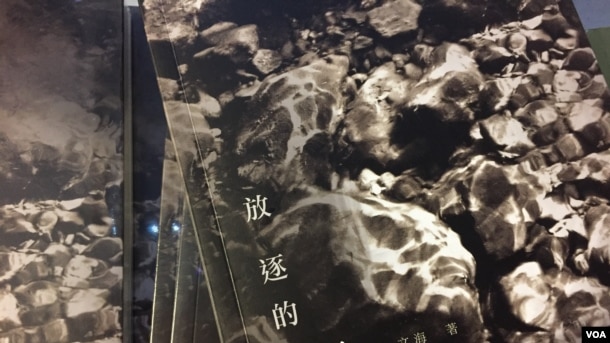
独立纪录片制片人文海新书(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此次工作坊由独立出版人、独立纪录片导演等授课,教授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以及自媒体和公民记者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推广作品。笔会请到了著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威尼斯影展入围导演文海先生讲述他的新书《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
文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1999年之后有质量和数量上的飞跃。
他说:“我自己的研究是从99年以后,整个的独立纪录片借助于便宜的器材、资讯的广泛展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本土电影节的建立,这几个条件的具备使得从99年到14年左右,这10多年以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人数、所设计的题材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90年代的。”
他表示,原来独立电影是属于圈子内的一个专业电影交流,然而通过艾晓明、艾未未等人的努力,通过互联网时代到来,变成了一个公民影像时代的到来。
然而他说,在2011年之后,整体气氛变得压抑,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独立纪录片电影节: 北京独立电影节 、南京中国独立影像节、还有云南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 到了201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不能公开活动了。在全面的打压和限制之下,现在搜集素材容易,但是传播却有很大的困难。
文海先生透过工作坊,向前来参与学习的公民讲述了拍摄独立纪录片需要注意的技术层面。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独立中文笔会在国际笔会促成下,由贝岭、孟浪发起筹创,于2001年7月成立。笔会的宗旨是“弘扬中文文学、维护言论自由“,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文文学,维护世界各地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尤其关注与救助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写作者,强调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政治干扰和迫害。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先生表示,很多流亡、异议作家和异议政治人士成为了笔会的荣誉会员,这样的情形使得笔会越来越像一个人权组织。但笔会有一个基本的宗旨,就要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所以笔会一直在这两个部分做艰难的平衡。
来源:美国之音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曾金燕、王藏获奖
据美国之音10月30日报道,“独立中文笔会”当天继续在台北国际艺术村举办纪念创会15 周年的系列活动,并以现场座谈和远程参与等方式与全球各地的公民记者和专家,共同探讨网络时代独立纪实文学影视创作的发展方向。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获得“独立中文笔会” 2016年度第12届“林昭纪念奖”;北京的80后诗人王藏成为今年“自由写作奖”得主。据报道,2001年7月成立的“独立中文笔会”宗旨是在弘扬中文文学的同时,致力于维护言论自由,并救助那些在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作者。该笔会现任会长贝岭表示,由于很多中国的流亡异议作家和政治人士已成为笔会荣誉会员,也使得“独立中文笔会”目前越来越像一个人权组织,所以笔会一直在致力于这两方面的平衡。
来源:自由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