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百年祭:《致命的列寧》在港台出版
瑞迪

溯源出版社2017年 3月推出《致命的列寧》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2017年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
孟浪:「2017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當然,現在的年輕人可能
法廣:這本書的內容並不全部與十月革命直接相關。為什麼?它的內
孟浪:「這本書書名是《致命的列寧》,實際上是我和一些朋友想做
《致命的列寧》由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策畫,由香港溯源出
法廣/2017/3/22
瑞迪

溯源出版社2017年 3月推出《致命的列寧》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2017年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
孟浪:「2017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當然,現在的年輕人可能
法廣:這本書的內容並不全部與十月革命直接相關。為什麼?它的內
孟浪:「這本書書名是《致命的列寧》,實際上是我和一些朋友想做
《致命的列寧》由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策畫,由香港溯源出
法廣/2017/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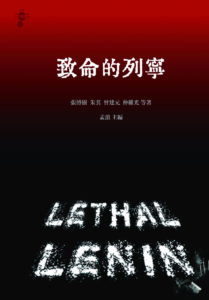

从美中各异的“一中政策”看川习交手
伦敦客
2017年2月9日川普、习近平通话,央视报道说习对川尊重一中政策表示赞赏,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同意“就共同关心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并期待“早日会晤”。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称这是川普对北京低头,是习川首次交手习获胜。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前中国美国商会会长齐默曼说法时,都以“纸老虎”、“被习搞定”来形容川从其原先质疑一中政策的强硬立场退缩,认为这将使今后华盛顿与北京交手更困难。但美国传统基金会沃尔特.洛曼则不以为然说,川普支持一中政策并从美国立场重申它,是件好事,但并不代表习近平赢了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一中政策并不是因为中国要我们这么做,也不是因为这是给中国恩惠,我们遵守一中政策是因为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因此川普打电话重申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胜利。
习并非胜利源于美中各异的一中政策
我不苟同时教授关于川是“纸老虎”、习是“胜利者”的结论。却很同意洛曼上述的说法是源于美中各异的一中政策。如果美国一中政策等同中国一中政策,就是两国一个一中政策,等于美国完全接受中共价值观,当然是习胜利;反之,习并非胜利。从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至今的四十五年来,正是美国一中政策不完全等同中国一中政策,才导致美中两个大国诸多博弈或对立,以此保障台湾安全而免遭中共吞并。正如2014年12月11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所说:“美国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对台湾地位的立场”。而“台湾”正是此博弈和对立的核心议题和最大客体(对象),但中共和台湾亲共派的“台湾是筹码是棋子说”并不客观、准确。如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新总统川普在他整个执政期间的一中政策,会有诸多不同前任的表现,完全有可能增大与中国一中政策的博弈或对立。这是习近平并非胜利和说习胜利为期过早的理由之一。
一中政策,美中各表
因中共外交等对外机构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时表现的一中原则(也称中国一中政策),往往用不分彼此你我的、唯一的一中政策表现,目的要他们服从中国一中政策而非别国认知、理解的一中政策。这个麻烦在中美间突现了,即美中之间出现了美国版一中政策与中国(也称中共)版一中政策。两个一中政策表现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相反的。美国这种“一中政策、美中各表”与大陆和台湾(共产党和国民党)“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情景相类似,全属正常和必然反映。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看到两者不同:
—–美国的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立场与中共“老三段”立场的根本对立
如同国民党认定一中是指“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那样;如同民进党认定一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国号目前称中华民国那样,川普前六任总统先后以美中《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的国内法、《美日安保条约》及相关法律效力公文或非法律效力声明、决议、函件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美国版一中政策。美方对《三个公报》里中国版的一中“老三段”第一段“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第二段“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从未予以“承认”而仅是“认知”。前美国副国务卿华伦.克里斯多福1979年2月认为美中《建交公报》这段英文是对美国有约束力条文“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指“美国政府认知了解台海两岸当时共同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华伦强调“并不因此承认它,认知并不代表承认”。依“老三段”结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事实上,台湾68年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管辖过,一党专制中共一天也未统治治理过台湾,即台湾从未隶属于大陆统治和占有,它从来是以主权国家名义为联合国创始国身份存在联合国二十六年,联大驱逐蒋氏代表出去的2758 决议也未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故华伦代表美方强调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是有理有据不争事实。但《三个公报》英文版把“尊重或认知acknowledged”写成“承认recognised”,把“中国人立场”写成“中国立场”;在《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文版上把“尊重或认知”也写成“承认”(除上海公报外)。这样故意曲解美方一中政策意思、意在强迫美方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方立场是很卑鄙无耻做法。2007年9月5日,美国致函联大秘书处,对潘基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说法,表示这不是美国一贯立场,而且,联大2758号决议并未谈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明确表示美国不接受潘这一说法。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实际就是美国一中一台政策最大反映。中国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国一中一台政策存在不少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对立及重大分歧。这次川习通话虽谈及一些议题,但未将中国一中政策横向展开,也未将美方一中一台横向展开,美中双方柔性交手谁也没有实际性结果。时教授、齐默克怎么盲目过早说习近平胜了川普呢?
—-《三个公报》成为中共一中政策基石;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七公报》,与《对台六项保证》一起成为美台关系基石
美国《台湾关系法》与《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同时生效。在一百七十三个与华建交国中仅此一例。中共除《建交公报》外未有国内法同时支撑;美国签署《建交公报》时,由卡特签署的《台湾关系法》的国内法支撑并与之同期生效。此法具有法律效力非同无法律效力的声明或公文。故美国政府曾声明说,对于台湾问题立场是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法律上优于《八一七公报》,它为美国法律,而《八一七公报》为政策声明。我理解它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石。而中国政府以一中原则为底线,认为该法“干涉”中国“内政”而执意游说美国国会修改或废除该法但至今未果。2016年7月,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88、38号共同决议案》,用书面表述六项保证,把它与《台湾关系法》一起成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尤其是第五项“美国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和第六项“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则是最坚硬的两基石!它写进共和党2016年党纲。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称之为“确保台湾不致于成为美中关系谈判的筹码”。三十七年来,中共一直把与《对台六项保证》同时生效的《八一七公报》加其他两公报形成的一中政策视为中美关系重要基石坚持至今。两个不同意义、不同目标的基石出现,正反映美中各异的一中政策不仅历史性地存在,而且将长期博弈下去。
川普旋风冲击中共一中政策
川普就职二十二天,大刀阔斧兑现竞选承诺,除进行保护美国贸易战准备和签署7国旅游禁令外,不发函邀请中共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发表“不受一中政策束缚”和抨击中共南中国海偷走美军器材等犀言、与世界二十多国家元首通话而迟迟未与中共党魁习通话、第一个接见英国首相梅姨和两次会见日本首相安倍等、都贯穿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轴线和发出一中一台信号。川普旋风猛烈冲击中共一中政策。美国防长马蒂斯访日时痛斥中共“摧毁了这一地区国家的信任”,再次宣称《美日安保条例》适用钓鱼岛,从而牵制中共军力部署间接保护台湾,并削弱共军吞台锐气。据“海军时报”引述数名美国海军官员指出,美军将派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前往南中国海,执行新一轮航海自由行动,甚至让军舰驶入中国人工岛礁12海里内,以确保美方在国际法下,军舰有在公海自由航行权利。这有待川普批准。如此计划实施,将共军海军注意力及军力相对部署在南中国海从而减轻台湾军力部署及军事压力。对缓和台海紧张局势有利。这些都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包括《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及《美日安保条约》等产生的旋风效果,也是美国一中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
美中不尽相同的通话声明亮明各异的一中政策
然而,川习通话涉及一些议题,但重点是〝一中政策〞。白宫发布简短声明,有港媒指出,川习通话时间较长,白宫用〝lengthy〞(长时间)表示,含翻译时间。声明特别提到,〝应习近平要求,川普总统同意恪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President Trump agreed, at the request of President Xi, to honor our〝one China〞policy)。从句式看,白宫特意强调习近平这一〝要求〞。
引人注目是这里的〝一中政策”并非中方定义的一中,而是美国坚持的一中政策,即除中美三公报外,还含《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和《美日安保条约》等。美国国会支持将《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上升至三个公报同等地位,认为这是美方〝一个中国〞政策基石。台湾《天下》杂志说,白宫声明用的honor有尊重,承认,许诺实践三层意思。又说白宫强调川普承诺,是在习近平要求下说出口的,如此直白的道出对方要求,在国家对外声明中,十分罕见。
中方声明呢?它称:〝川普强调,我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显然,北京声明的川普表态,突出〝奉行一中〞,“充分理解”,强调一中是两国政治基础,保持这个中美既有的大看点。但声明字里行间存在不同涵义。白宫声明强调,两位领导人都发出邀请对方互访,彼此期待继续对话,以取成果。而中方声明只凸突两位领导人期待早日会晤,并未强调〝互访〞。
从美中声明看:我认为是习等了二十二天等不及了非要主动与川通电话而不是川等不及了非要与习通电话,习是主动者川是被动者;是习以国家名义发出外交礼请(口头或书面),川是受邀接应,即使再有要事难处,鉴于外交对等原则和礼仪,也必须安排接触;是川亮出上述美国自己一中政策内涵定义与中方不尽相同之处,凸显美中各表;而无论中方声明中语气轻重淡浓、平铺犀利如何,美方会以外交礼仪予以表述而不失自己一中政策立场。这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都难以得出川普是“纸老虎”习近平是“胜利者”的交手结论来。
2017/02/14
从九十一高分点展望“一中一台”
伦敦客
美国“自由之家”2017对世界一百九十五个国家和十四个地区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度,分别从最自由一分到最不自由七分、另设综合分(满分一百,分數越高自由度越高)进行评估显示,全球自由度连续十一年下滑,六十七个国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度2016呈倒退趋势。政治权利中国得“最不自由”七分;香港得“部分自由”五分;台湾得“最自由“一分。公民自由度中国得“不自由”六分(西藏得“最不自由”七分);香港得“自由”二分;台湾由2015的二分上升到2016“最自由”一分。中国综合分为十五分(西藏仅一分,比三分的北韩还低二分),比2015下降一分,继续列为“不自由”国家;香港为六十一分,比2015下降二分为“部分自由”;台湾比2015提高二分为九十一分。这个九十一高分让台湾连续十七年列为全球自由国家行列。
自由高分亮出“一中一台”
为何二千三百万人台湾与十四亿人大陆自由度悬差六倍(七十六分)?这非国民党、民进党、其他两岸利益组织评估,而由七十六年经验及权威国际非政府组织评定,应该客观公平。在全球尤其中国自由度连年下降、人权记录越趋恶化下,台湾鹤立鸡群,不降反升,以亚州第二自由分(次于日本),让国际社会、世界人民刮目相看:此分凸显了一个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一个民主台湾的现实剥离、实际分治的客观存在,亮出了“一中一台”的客观存在。让她有理由、有资格挑战中共“一中原则”。
“一中原则”的脆弱性
三段论的“一中原则”始于驱逐蒋氏代表出联大的1971年。为反制“苏修”摆脱外交困境;为破坏台湾传承文化摆脱文革困境;为拉拢众多国家建交孤立台湾,中共走的是外紧内松机会主义建交路线。把一中原则降低到只要不承认台湾不与它建交就可与己建交,而不去严格审核、摸清建交国对中共一中原则态度如何。截止2016年3月与中共建交的一百七十三个国家,大部分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尊重、认知“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但并未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或一个省。这些国家如欧盟、法德葡意比荷加等,中共毅然与之建交;而土耳其、伊朗、爱尔兰、奥地利、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等三十二国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政府,而建交公报竟然未提及台湾,中共也睁一眼闭一眼与之建交;更有孟加拉、利比亚、墨西哥等八国的建交公报中只提某日建交换使,其他什么主要内容都没有也可建交;仅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诺不是中共降低建交门槛,一百七十三个建交国中会有相当数量国加入台湾邦交国行列而非今日二十一国。可见“一中”虽是中共建交原则前提,但为政治目的、利益需求中共也会随时牺牲原则前提换取建交国数量,仅为缩小外交空间压垮台湾。这正是“一中原则”脆弱性大暴露,越来越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质疑:其“合法”存活期还剩多久?
美国从未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三公报喜见“一中一台”端倪
纵观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公报》、1982年《八一七公报》,美国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仍保留与台湾非官方往来条款,并在三公报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表述时,不用英语“recognize”一词中文表示的“承认”;而用英语“acknowledge”一词中文表示的“认知”,意在台湾虽是中国一部分,但美国并不表示“承认”只是“认知”,机智地将“认知”与“承认”人为区分,以示其巧妙而模糊的对台态度。如《上海公报》写道“美方认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均主张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但中共在《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文表述时,一改上海公报的中文述法,将美方的“认知”统统换成“承认”;后来,又将“the Chinese position”的“中国人的立场”错写成“中国的立场”,抽掉“人”字。这种偷梁换柱拙劣做法歪曲了美方对台地位“认知”的巧妙而模糊态度。即便这样,六十七年来,含上述三公报的任何场合,美国从未recognize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或一个省,并一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强硬立场未变。此立场贯穿三公报全文。美国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三公报里有“一中一台”端倪。
《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核心是“一中一台”
美国1979年1月与中国建交三个月后,通过国会制定十八条《台湾关系法》并与中美《建交公报》1月1日同时生效。两个互反行为文件同时生效,这在一百七十三个与中国建交国中仅此一例,它凸显美国对台湾安全高度重视和特别保障。该法第2条乙款第1项规定“维持并促进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以及中国大陆暨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广泛、密切与友好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它告诉世人,对台湾是一样地发展除与中国官方政治关系外的一切社会关系,而非中断与台一切关系。该第4、6项规定“任何试图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经济抵制或禁运,决定台湾之未来,将被认为乃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一项威胁,为美国所严重关切”;“维持美国之能力以抵制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之武力行使或其他形式之强制行为。”这些告诉世人,一旦中共武力攻台,美国绝不会背信弃义、坐视不管,而是依此款武力帮台粉碎共党企图,保护自由之土免遭独裁践踏。故这是一部规范美国对台政策、确保台海稳定和平的美国重要国内法。为有效保障《台湾关系法》实施,1982年8月,里根总统在与中共签署有关武器售台的中美《八一七公报》同时,效仿1979年1月前任卡特总统签发两个文件同时生效那样,在公报发表次日的8月18日,由台湾发布经里根与蒋经国商谈形成的《六项保证》;2016年5月16日在蔡英文就职总统前夕,由美国众议院通过书面《六项保证》即“不会设下结束对台军售日期;不会更动台湾关系法条款;不会军售前与大陆协商;不会做台湾与大陆调解人;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立场;不会承认中国对台湾主权”。以此为献给蔡的就职礼物。令人惊奇是最后5、6项才是最重要保证。这个不改变美国对台主权立场和不承认中国对台湾主权态度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保证!“六不会”的《六项保证》条条清晰、泾渭分明、保证剔透!这里台湾、大陆,两个政治实体被剥离得清清楚楚。《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核心就是一中一台!在美国眼里,台湾是自主独立一天也未隶属于中共统治的主权国家;中国是被中共统治六十八年的独裁专制的共产国家。九十一自由高分的台湾岂能让十五低分的中共欺负蹂躏?!一个把尊重台湾主权当作尊重自己主权的美国,最有力量、最有资格对中共“一中原则”和武力吞台说“不”。由“不”催化成的“一中一台”,中共岂能不负隅顽抗?
习军国主义备战和亲共派叫嚣反推“一中一台”前进
“一中原则”最大目的之一是将民主台湾统一到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蔡英文八个月新政未让习近平看到和统曙光,故武统战鼓必从习处擂响。始2013“从严治军”到2014揪军中老虎到2015大阅兵直至2016年七大军区改制五大战区、任命五大战区司令员政委(专打台湾的东部战区司令员刘粤军是对越反击战有实战经验连长);组建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领导班子;又将钓鱼岛主权、南中国海危机、武力攻台三事列入国家战略安全考量,故必须贯彻习“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着眼点”和“各战区要随时准备领兵打仗,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等指示。基于备战打仗,习嫌军委主席不够,除兼十个专门组长主任外,另兼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和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专家分析是直接冲着钓鱼岛、南中国海、台海来的。台湾岛内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吹捧中共在“点穴战、巡航导弹和美国放弃台湾优势下二、三天拿下台湾,林是表面点评军事、打着研讨旗号、骨子里盼共军早日接管台湾的共党内应。我看过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里林中斌帮凶、武力攻台鼓手李毅完全同意林的胡说,恫吓五天拿下台湾;并对蔡英文2019前接受九二共识无望,期盼2020共军武统台湾,是个一心希望共军血洗台湾的台籍带路狗。那个赖岳谦左个大陆购买力世界第一,右个台湾青年对大陆好感增加,中间是共产党政权稳定,这些连习都不说的被赖抢说了,他也认为三至七天拿下台湾。赖教授身份与他不齿言论让两岸人民跌破眼镜。我完全支持台湾民报评论员郭宝胜以一战三、痛斥亲共吞台派无耻言论的正义行为!亲共派甚嚣尘上的武统表演,除他们接受大陆统战洗脑和借台优越民主环境亮身外,主要是被习2016一系列军国主义备战吓坏的。资料显示:8月海军三大舰队在东海举行实兵实弹对抗演习和空军轰-6K、苏-30等多型战机飞赴南海战斗巡航;12月辽宁航母编队驶出第一岛链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和后来两次绕台炫耀武力;9月中方4000官兵参与中俄2016海上联合对抗演习;7-9月北部战区内蒙古朱日清跨区基地化陆军最大演习;10月中部战区河南确山“利刃”大型陆军演习;11月歼-20隐身战机首亮珠海;7月200吨大型运输机运-20装备部队。上述行动概括一点:中共关注台湾,非常在乎台湾,台湾问题牵系“一中原则”成败。难怪习近平会见亲共红人洪秀柱后担心说:“如果我们不处理台独我们会被推翻”。此话道出中共危机重重、唯恐政权丢失和“一中原则”统一台湾破灭的心理和困境。正是这样心理和困境反推着“一中一台”前进。
自由是“一中一台”动力,展望川普团队成为好推手
2016年12月11日,美国侯任总统川普在电视访谈中提到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日通话时称:“我完全了解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跟中国在其他问题、包括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受缚一个中国政策?”此话是川普直接挑战中共“一中原则”(政策),打破三十八年历届总统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沉默,对世界和平和人权发展是大跨步。
川普告诉我们,中共“一中原则”不是永恒不变基石,今后他要用台湾这块牌来反制中共对蔡新政打压,迫使中共贸易让步,否则随时弃一中逼中共在台问题让步。因为川普已将昔日历届总统对台的模糊遮布撕开,将中共一中弊端祸心全暴在阳光下,赢得了美国、台湾人民欢欣和支持。蒂勒森新国务卿及数十位鹰派任职,标志世界秩序、政治格局、美国力量、一中原则、台海态势等将会改变。他们是川普新政铁杆也是亲台疏共派。由他们在川普手下执政,会恪守《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一中原则”会倍受挑战,“一中一台”会越加明朗!
美国《防务新闻》驻台北记者颜文德为美台军事关系改善不引发战争,汇整台防务分析人士、前任美台军方人士及国防产业界意见后所写的“十个建议”,非常及时有用。
我将之缩写为:准美现役海军将官观察汉光演习/准台空军参与美空军红旗军演/准台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管控美台间1.5轨活动/准美台彼此办事处挂旗互邀政府官员活动及准双方公开穿军服/提升在台协会层级/促进美国务院国防部副层、现役星级军官挂在台协会头衔定期访台/开启美台民间交流项目/准台军官入美军事学院及训练/美完成对台军售,并为台自制潜艇提供方便。
“十个建议”浓缩了川普新政推动“一中一台”前进的智慧、策略及部署,是其让美国再次伟大计划一小部分,也是前总统奥巴马卸任前签署2017国防授权法产物。不管习高兴不高兴,“十个建议”方向短时间不会被抛弃。我衷心期待川普团队能够成为推动“一中一台”前进的好推手!不久美将向台出售六十架F-35B短程垂直起降战机和一百五十架F-35A传统战机,这正是迈出“十个建议”第一步,也是“一中一台”迈出的新一步。
從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戰後國際納粹審判──關於阿倫特的「惡之平庸」
還學文
「惡之平庸」在西方──紛爭不息半世紀
最近德國司法部長馬斯(Heiko Maas)親自推出司法部一個歷時四年的專案研究「羅斯堡檔案──聯邦德國司法部和納粹時代」,研究揭示了當年聯邦德國司法部與納粹德國司法人事上的連續性:到1970年代聯邦司法部高級官員一半以上曾是納粹黨員,其中五分之一甚至是黨衛軍或直接從納粹司法部進入聯邦司法部。這些人跟耶路撒冷受審的艾希曼類似,手不刃血的納粹官僚──半個世紀之前漢娜‧阿倫特著書立說以「惡之平庸」為之辯解的那些人。與阿倫特相反,五十年來戰後德國成長出嚴肅面對納粹歷史和清理納粹罪惡的政治文化。今日的聯邦司法部長對共和國司法部這一段歷史公開表示痛心,進而強調:值此人權與法制國家又遭質疑之際──當時是指國際難民危機之前,如今再添公開挑戰普世價值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情勢之下,正視這段歷史尤為必要;每一個公民尤其是司法工作者,必須明確並且不斷地捍衛憲法的基本價值。
與在原產地的遭遇大相徑庭,漢娜‧阿倫特「平庸的惡」一詞在大陸和海外中文世界耳熟能詳時髦多年經久不衰,拿來標籤國人以及社會的弊端,而不在分析和批評罪惡本身,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儘管資訊昭昭之今日,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並不難做到,一個大致的如實瞭解不過是查字典的功夫,而求實的瞭解是對有意義和負責任的言說的基本要求。
中文「平庸的惡」是一望文生義的誤譯,接下來以訛傳訛就不奇怪了。該詞的原意及其持久的爭議中文文章中很少見到,偶有另類聲音也被盲目追捧阿倫特的潮流淹沒。
阿倫特原文的說法「惡之平庸」,從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個關於惡之平庸的報導》一書1963年問世就爭議蜂起、歷經半個世紀而不息,持續至今。人們質疑、爭論和批評阿倫特對納粹艾希曼「平庸」的定性,五十多年來的批評不斷地提出新的證據一再表明,艾希曼犯罪不是因為平庸。
並且「惡之平庸」不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論題之一,阿倫特書中對艾希曼的辯護—從「平庸」以至「無罪」,直指戰後納粹審判,從她親臨的耶路撒冷直到在先的紐倫堡審判。
本文通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阿倫特「惡之平庸」的文本以及關於「惡之平庸」的爭論,呈現這一說法以及西方社會反應真實的一面,從而中文讀者有可能據實瞭解和評價阿倫特及其「惡之平庸」。
西方社會對「惡之平庸」的爭議──中文傳播的盲點
中文「平庸的惡」傳播的盲點首在迴避了西方關於它的爭論,畢其半個世紀的歷史,「惡之平庸」一說始終備受爭議。不僅西文文獻汗牛充棟,辭書也必備及,例如大英百科全書「漢娜‧阿倫特」條目中即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為其「高度爭議」的作品,而這,是西文辭書類於此的標準陳述。
關於這一爭論,「惡之平庸」問世五十年《紐約時報》上兩篇文章。一篇是影評「新電影再現漢娜‧阿倫特與『平庸的惡』」[1],原文標題實際上是「那個在惡中看出平庸的女人」(The Woman Who Saw Banality in Evil),以下簡稱「影評」。另一篇是書評「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惡」[2],評介德國女作家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新作《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殺者未經過審視的人生》英譯本(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2014)發行,以下簡稱「書評」。斯坦尼思發現, 人們「浪費很多時間等待驚人的新資料,而沒有坐下來仔細查看已有的資料」,這一批評首先就適用阿倫特本人及其對艾希曼平庸的論斷。
下面的摘要可以使讀者對於「惡之平庸」的激烈爭議有個印象。
關於對阿倫特「惡之平庸」論戰的歷史:
阿倫特的「惡之平庸」在知識分子中「挑起了『一場內戰』,引發了惡毒的爭論,毀掉了一生的友誼」,「人們把這場不斷升級的爭論稱為『論戰』」,而電影《漢娜‧阿倫特》(2013)「再度啟動了那些辯論和那個時代」 。(見影評)
關於對阿倫特及其「惡之平庸」的批評:
「傑出的以色列記者阿莫斯‧埃隆(Amos Elon)總的來說是支持阿倫特的,不過他在介紹她書的平裝版時說,阿倫特『習慣於依靠不確鑿的證據得出絕對的結論』」,而「艾希曼是平庸的這一結論所依據的不確鑿的證據,就是他在證人席上充滿陳詞濫調的自證」(見影評)。
這樣的批評應不是個別人的偏見,嚴肅學者如著名德國當代史專家蒙森(Hans Mommsen,1930年-2015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中指出,書中「一系列判斷未經充分的批評性檢驗」[3]。
斯坦尼思引用大量資料表明,「 1962年被判絞刑處死的艾希曼,絕不像他自己在審訊中所聲稱的那樣只是一名服從命令的公務員,而是一個狂熱獻身納粹事業的納粹黨人」。斯坦尼思說,她 「沒有打算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寫一本書,只是想用史實跟阿倫特辯論」,「書評」引用埃默里大學歷史學家黛博拉‧E‧利普斯塔特(Deborah E. Lipstadt),「如果說之前的研究者們嚴重削弱了阿倫特的論據,那麼斯坦尼思則『粉碎』了它」(見書評)。
以上評述值得認真對待,在於它們與相關其它文獻記載一致,並能夠由間接文獻或直接資料佐證,例如如阿倫特自己的文字。
「Banality of Evil」的翻譯──「平庸的惡」為誤譯
讀者或許已經注意到,前面與「平庸的惡」並列還用了「惡之平庸」,兩個說法形式和意義都不一樣,中文「平庸的惡」是誤譯甚至謬譯。
一、「banality of evil」是「惡之平庸」,非「平庸的惡」或「平庸之惡」
阿倫特的英文原文為「banality of evil」,語法上「banality」/「平庸」是主詞, 「banality of evil」指稱「惡」之性「平庸」。中文「平庸之惡」則相反,指稱「平庸」之性「惡」,更有中文論者自造英文「evil of banality」與其中文「平庸之惡」對應[4],可為誤譯之證。「平庸的惡」還可解為以「平庸」限定「惡」、指惡之一種 ,或可英文硬譯為「banal evil」,德文硬譯為「banale böse」── 筆者孤陋,尚未遇見德文這種說法。
從原文出發,對於「Banality of Evil」,中譯「惡之平庸」原則上合意,「平庸之惡」不合,「平庸的惡」 則謬。中文世界對阿倫特「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誤讀和誤解,即是從「平庸的惡」或「平庸之惡」這樣的誤譯開始的。本文將視不同語境,援引三種譯法。
二、惡vs.平庸──「banal」的含義
那麼,詞義上「Banality」譯為「平庸」是否貼切呢?「Banality」的形容詞詞根「banal」,意為平常、無聊、司空見慣,乏味、陳腐、平淡無奇……,是對事態定性的描述,如阿倫特說納粹‧艾希曼服從、盡職、無思想、只關心個人前途為「banal」—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是在中文裡「平庸」不僅作為客觀描述更常有主觀評價在內,例如說某人平庸就主要是對其個人氣質抽象的貶義評價。對應「banal」的常見含義,中文「平庸」之譯就未必合適,因為沒有體現「banal」基本的描述性意義。翻譯要能夠既貼切又簡潔不容易,「Banality」譯為「平庸」雖言簡卻不意賅,「庸常」或許貼切一些。一定要用「惡之平庸」的譯法,則不可不知道「平庸」與原文意思上的距離,不可不在論述中廓清和補足原意。便利起見,本文從俗沿用「平庸」。
追究「banal」的語意是因為直接涉及到「惡之平庸」爭論焦點,「惡之平庸」引發爭議不可避免:惡竟然能夠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嗎?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前後
「惡之平庸」不是當作學術概念而是在阿倫特作為記者的報導中提出的,它的由來決定了社會對它的反應及其後關於它的爭論。
「惡之平庸」出於漢娜‧阿倫特是在半個世紀前,1963年。1960年5月11日匿藏阿根廷的德國納粹艾希曼被劫持到以色列。涉及艾希曼的劫持,《紐約時報》的斯坦尼思書評中提到,「西德官員不太願意將艾希曼和其他前納粹分子繩之以法。根據德國《圖片報》(Das Bild)2011年公布的機密檔,西德官員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處」。並且,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消息,以色列不是發現而是得到,不是從德國政府而是而是從德國奧斯維辛審判檢察官鮑爾(Fritz Bauer,1903-1968)那裡[5],鮑爾心裡清楚艾希曼絕不會被引渡到德國受審,冒著走漏風聲會以叛國罪論處的危險,將消息秘密傳遞給以色列政府。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審判在耶路撒冷開庭,12月15日宣判;艾希曼上訴被駁回後,1962年5月29日終審判決,6月31日處決。這是繼1945年紐倫堡審判之後對納粹的又一世紀性審判,各國記者雲集耶路撒冷觀察報導,阿倫特也在其中。書稿完成於1962年秋季,1963年2、3月間,以題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的系列在《紐約客》「記者自由談」(A Reporter at Large)專欄發表,文稿修訂後1963年5月在美國出版,冠以副標題「一個關於惡之平庸的報導」。一年之後,1964年該書增訂再版,是之後被廣泛引用的版本[6]。
德文本同年出版,是跟進最快的外文版。因為艾希曼身為納粹而被阿倫特宣稱視之平庸如常,《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出版的意義自與其它文本有別。皮珀出版社(Piper)主持該書翻譯出版的勒斯納(Hans Rößner)和艾希曼一樣是典型的辦公桌前的納粹──戰後德國對那些納粹官僚的稱呼:也是黨衛軍少校,出任過納粹政府人民文化與藝術處主任,也在帝國安全局(RSHA)任職。身為猶太人,阿倫特的「惡之平庸」傳達了法庭上納粹‧艾希曼的自辯,表達了許多與艾希曼經歷類似的納粹的心聲──懾於盟軍佔領當局的政治壓力而不得公開表達[7],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代言之功是正當其時。這本書當年在德國的遭遇,依德國當代史學專家蒙森的觀察是「壓倒地被排斥」,而「積極的反應又都來自錯誤的方面」(見《惡之平庸》德文本「蒙森序」,同注3),這個一正一反的對比足以說明問題,無須任何畫蛇添足的詮釋。
1986年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增訂版版本簡介,「庭審報導──初在《紐約客》上連載、繼而成書出版──引發了一場雪崩。德國當代史教授蒙森的序言分析了艾希曼審判的歷史和阿倫特報導引起的爭論」。作為專門研究1918-1945年從魏瑪共和國到第三帝國時代歷史的德國當代史專家,蒙森有專著研究納粹德國的官僚制度,他對阿倫特一書評論的權威性自不待言。蒙森出身德國歷史學世家:曾祖父特奧多‧蒙森(Theodor Mommsen)是德國古代史專家、德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1902)得主,父親與孿生兄弟也是德國歷史學家。作為德國1986-1987年當代史爭論中保守的自由主義一翼,蒙森序可視為這一歷史爭論的產物,是對那種掩飾納粹德國歷史企圖的一個嚴肅的回應。筆者閱讀的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1986年增訂版,徳譯經阿倫特本人認可,故可取信;本文直接引文還是會對照英文原文,翻譯中總會發生改動,而改動總難免隨意。
不言而喻,阿倫特的猶太人身份,影響了爭論的色彩。當年對「惡之平庸」直接而尖銳的批評多出自猶太人,非猶太人批評者可以理解地選擇了克制、距離和極盡善意的理解。支持一方的見解,以筆者所讀,多是為阿倫特背書,例如「惡之平庸」概念深刻可惜選錯艾希曼為例的說法。這卻錯愛了阿倫特,她談論「惡之平庸」不是從概念到實際,用她自己的話是「嚴格限於事實層面,指示一個現象──審判中盯住一個人的臉所看到的」。
艾希曼「惡之平庸」的標新立異為阿倫特帶來轟動,也毀昔日的友情於一旦。國際著名猶太學者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也是德國猶太人,192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尖銳批評「惡之平庸」的說法輕易抹殺了罪犯與受害者的區別,直言阿倫特對於猶太人非人的苦難幸災樂禍與冷酷不仁的語調簡直是變態,兩人二十幾年的通信關係於1964年終止。是否批評者頭腦發熱、不夠寬容、過於挑剔呢?依德國人蒙森,「面對這個題目深刻的悲劇性,阿倫特那種尖酸與咄咄逼人的態度是失當的」(見「蒙森序」)。閱讀中,筆者亦屢屢為作者尖厲的冷嘲刺激而不能自己,對她的議論時時不禁難以置信難以理解難以接受,始知肖勒姆不為過分。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抨擊「惡之平庸」抹殺了納粹種族滅絕的罪惡,許多阿倫特曾經的猶太友人和猶太人社團對她背轉身,一直到她離世。
「以賽亞‧伯林在《伯林談話錄》中說:『我無法接受阿倫特的邪惡之庸常性的觀點,我認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是荒謬的。納粹並非庸常之人。艾希曼深信他一生中做過的主要事情是對的。我問過肖勒姆為什麼人們欽佩阿倫特女士,他告訴我,任何嚴肅的思想家都不會這樣做。那些欽佩她的人,只不過是會擺弄字母的文人,他們不用腦子思考。』」[8]。嚴肅學者蒙森批評阿倫特論述隨意,「以歷史學精確而完整的資料分析來要求,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書中許多論斷都不能成立。一系列判斷沒有經過充分的批評性檢驗,有些推論則表明作者對於1960年代初已有的資料所知有限。……作為記者,阿倫特時常使用一些要經繁複的歷史分析、大部分還有待接觸到文獻才能確認其真實性的材料」。儘管審慎而克制的表達,蒙森的批評足以致命:「確鑿的歷史陳述既非作者所願,也非作者專長」(見「蒙森序」,同注3)。
阿倫特轟動推出「惡之平庸」並再三聲稱:那是報導,既非理論更非學說。但報導的力量在於真實客觀,而艾希曼「惡之平庸」的斷言卻是從作者的相信和想像產出的。她甚至不諱言,她的艾希曼審判報導無關納粹種族滅絕的滔天罪惡,只聚焦被告艾希曼作為有血有肉的個人[9]。對於這一主題沉重的歷史題材,阿倫特的處理所欠缺的不僅是學術與新聞的而且還是基本的道德的嚴肅性。
回到文本──阿倫特的「惡之平庸」
回到文本不僅重要而且根本,文本是理解和討論阿倫特「惡之平庸」的基礎和根據;背離文本,一切都無從談起。
一、 「平庸的惡」 作為中文詮釋
常見中文用「平庸的惡」,說艾希曼既不奸詐,也不殘暴,只是服從、盡職、謀求晉升,也不想自己在做什麼,無思想而犯下滔天大罪;說是「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
除了「平庸的惡」的誤解,以為阿倫特背書而言,這種說法大致不錯,但是說艾希曼因平庸而犯罪卻不是阿倫特的意思。恰恰相反,阿倫特的「惡之平庸」是說艾希曼的所作所為平庸而已,因此才有對她為納粹漂白罪惡的批評,才起了爭議。與阿倫特從惡中見出平庸的論斷相反,由平庸而至罪惡的推論是中文「平庸之惡」的思路。並且,「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的說法也不通:犯罪指因犯法而被懲處的行為,因此無責不成罪、無罪不刑罰;「無責任犯罪」則自相矛盾。如果「被意識形態裹挾」是無思想因而犯罪無責任,豈不所有認同納粹意識形態的罪犯都可以無責無罪的名義要求無刑罰?事實上這個不通起於漢娜‧阿倫特、她的「惡之平庸」、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陳述,然而對她的盲目崇拜阻斷了國人的思考與追問。
二、 「惡之平庸」文本──阿倫特的艾希曼圖像
如果不是艾希曼,就沒有阿倫特的「惡之平庸」—那是她審判中盯住艾希曼的臉所「看」到的,也不會有之後那些激烈而經久不息的爭議。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告」(The Accused)一節中,阿倫特對艾希曼之「平庸」有充分的描述,儘管沒有使用這個詞。「後記」一節中專有一段談艾希曼的「惡之平庸」,所見引用多源於此。閱讀阿倫特這段原文或者譯文,對使用和介紹「惡之平庸」是必須,沒有經過這個必須,「平庸的惡」無批評的濫用自然不奇怪。
「後記」中這段「專論」是這樣的:
「顯然,被告、被告行為的性質以及審判本身所引發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都遠在耶路撒冷法庭考慮之外。在『跋』中我嘗試探討其中一些問題,那不再是一篇簡單的報導。如果人們覺得我處置不當,我並不意外並且歡迎對整個事件的普遍意義展開討論,越是直接針對具體事件越有意義。我可以想像,真正的爭論是關於本書的副標題,我談到惡之平庸嚴格限於事實的層面,指示一個現象──審判中盯住一個人的臉所看到的。艾希曼不是伊阿古(Iago,莎士比亞《奧賽羅》中的奸佞小人──筆者注),也不是馬克白(Macbeth──莎士比亞戲劇中人,個性兇殘,筆者注),再沒有比『一心做惡人』的理查三世距離艾希曼的心靈更遠。除了竭力求晉升,他再無其他動機;而且這種進取心也不犯罪,艾希曼又不想謀殺上司、攫取他的位置。說白了,他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嚴格說他缺乏想像力,以至於能夠連續幾個月坐在角落,面對審訊他的德國猶太人傾吐心愫,不厭其煩地解釋他為什麼只做到黨衛軍中校,未獲晉升真不是他的錯。原則上,艾希曼一切都很清楚。在對法庭的最後陳述中他談到『國家確立的價值重估』,他並不愚蠢。他就是沒思想──跟愚蠢不同,這種無思想注定他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大的罪犯之一。說來乏味(阿倫特用的是「banal」,筆者注)甚至好笑,即使以世界上最純正的意願,也無法從艾希曼那裡發現任何深刻的惡, ……這種不現實和無思想會比人惡的本能加在一起更造成災難。這是一個教訓,既不是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也不是關於它的理論」。
關於「惡之平庸」的爭論暫且不論,超越爭論始終與阿倫特保持友誼的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她的博士論文導師雅斯貝爾斯,從一開始就不接受她認為艾希曼平庸的觀點。1961年6月8日,雅斯貝爾斯給阿倫特的信中寫道,「現在你又回到以色列。此間,艾希曼顯出另一面,個性的殘忍。畢竟是一個行政謀殺的官僚,能絲毫沒有非人的品質……?對這個人做出真正恰如其分的描述,對你絕不輕鬆」[10] 。艾希曼審判歷時十三個月,紐倫堡審判一審歷經一年,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一審二十個月,阿倫特論定艾希曼「惡之平庸」不足一個月: 1961年4月11日審判開庭,5月7日她帶著艾希曼平庸的結論離開耶路撒冷。
「被告」一節中,阿倫特說有一大把心理醫生鑒定艾希曼「正常」,對待婦女兒童甚至堪稱典範。豈止艾希曼而且戈培爾,不僅舉止優雅而且富於人道──雅利安人以外的一切「非人」不在此例。阿倫特認為以謀殺罪起訴艾希曼是個錯誤,她毫無糾結地接受了艾希曼的法庭自述:我絕不仇恨猶太人、從來沒有殺害過猶太人、和謀殺猶太人根本沒關係,相信艾希曼「絕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他從來沒有要殺人」。阿倫特抱怨,「沒有人相信他。公訴人不相信他,因為這不是他的責任」,「法官不相信他……寧願由他偶爾說謊就斷定他是一個騙子」,雅斯貝爾斯的忠告毫無用處,阿倫特願意相信艾希曼。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她對艾希曼同情的理解與對猶太受害者以及「戰勝者」審判不滿責難之間不加掩飾而充滿激情的對立,每每令人瞠目結舌。
阿倫特關於「惡之平庸」及其爭議
1964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再版修訂「後記」中阿倫特明白確認了對「惡之平庸」的爭議,並且反覆重申此乃她的一個說法,不是什麼理論。提出這兩個要點,希望中文論者和讀者一來瞭解對「惡之平庸」的爭議確有其事,再則,「惡之平庸」不是理論。
一、對爭論的態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1964年再版時,阿倫特在「致讀者」中提到,「後記」中增加了有關爭論的議題。關於對「惡之平庸」的爭議,她說,「我可以想像,真正爭論是關於本書的副標題」、「如果人們覺得我處置不當,我並不意外並且歡迎對整個事件的普遍意義展開討論」。在這段文字之前,「後記」一開始阿倫特甚至用了「有組織的圍剿」、「操縱輿論」這樣的論戰字眼,爭論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在自由社會一個爭論綿延半個世紀而不絕,顯然不可能始終有組織地操控。
「惡之平庸」 半個多世紀的爭論歷史足以表明一個簡單的事實:這個說法沒有被普遍接受和一致肯定、不是定論、不是教科書、更不是經典。「平庸之惡」的中文論者對此先要有一個基本的瞭解,而後言說和論斷。這種必須的功夫可惜大多中文論者那裡基本上省略了,以誤讀傳播誤解因此無可避免,此其一。
二、「惡之平庸」既非學說也非理論
中文讀者、尤其是中文論者不能不瞭解,「惡之平庸」不是理論,阿倫特自己書裡、書外反覆重申。「後記」中她說,她的報導「不討論猶太民族這一空前的民族災難、不闡述極權主義、也不考察第三帝國時期德國人的歷史,更不是對惡之本質的理論分析」;「惡之平庸」「是一個教訓,既不是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也不是關於它的理論」;說她談論惡之平庸「嚴格限於事實層面,指示一個現象──審判中盯住一個人的臉所看到的」。幾乎同樣的內容,多年後她再度重申,「幾年前報導耶路撒冷艾希曼審判中我談到,『惡之平庸』──既非一種理論也非某種學說,而是指非常實際的一種現象──惡行」[11]。然而,惡行是事實而不是任誰可以隨意從誰臉上解讀的什麼;前面提到的斯坦尼思女士就是「想用史實和阿倫特辯論」,表明艾希曼不是她從他臉上看到和解讀的那樣。
三、阿倫特的「平庸」非常解
1964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出版,阿倫特應邀出席出版宣傳活動。在與她的廣播談話[12]中,菲斯特(Joachim Fest,1926-2006,《法蘭克福彙報》副刊資深主編、《希特勒傳記》作者)提到「惡之平庸」引起許多誤解,阿倫特對此表示意外。她說,人們以為「平庸」是普通尋常平淡無奇的意思,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絕不是說,艾希曼就在我們中間、我們每個人內裡都有個艾希曼!(那種平庸隱含和導致罪惡的中文詮釋毫無根據,阿倫特根本不是這個意思)要是聽到某人對我說一些聞所未聞非同尋常的東西,我會說,異乎尋常的平庸!我說平庸如同說卑劣(minderwertig,意殘、次、劣、賤等),我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平庸的[13]。「平庸」即「卑劣」?思維同一律和語言共同體的共識,對阿倫特一概不必?公共言論不是變戲法,阿倫特教人如何能認真對待?
無論如何,阿倫特「惡之平庸」的說法不是理論,是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中文世界為「平庸之惡」的後理論建構—從《極權主義的起源》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從「平庸之惡」回溯到「極端之惡」的種種 [14],既然無根據也就無意義。摘章引句,雖捷徑亦歧途。
阿倫特的艾希曼想像
艾希曼1906年出生,1932年在奧地利加入納粹,1934年納粹在奧地利政變失敗被禁,艾希曼逃往德國,1936年起任職納粹特別處理猶太人問題的部門。1939年帝國安全部(RSHA)成立後他負責猶太人「移民」,1941年猶太人被禁止移民,遷移局改為「猶太人局」,亦稱「艾希曼局」。1942年艾希曼出席了納粹 「最終解決」 猶太人的萬湖會議,作為局長他負責和主持實施了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計畫,遣送猶太人到德國和納粹佔領下歐洲各地集中營和死亡營的命令皆從他的辦公室發出。
阿倫特書中「被告」一節援引艾希曼的庭上辯白,「我和屠殺猶太人沒有關係。我沒有殺過一個猶太人,也沒有殺過非猶太人,我根本沒有殺過人。我沒有下令殺猶太人,也沒有下令殺非猶太人。我統統沒有做過」。阿倫特於是斷言:艾希曼「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缺乏想像力,沒有思想」,「誰也無法從艾希曼那裡發現任何深刻的或是魔鬼的惡」;阿倫特深信,「他絕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他從來沒有要殺人」。
「被告」一節中阿倫特轉述艾希曼律師以不違犯納粹德國法律為由的無罪辯護:說艾希曼那些行為不是犯罪,而是他國無權審判的國家行為,而服從國家是艾希曼的義務,「勝了受到讚美,敗了就被絞死」[15]。阿倫特幾乎持同一觀點甚至更強,「不可否認,這種犯罪是在一個『合法』的秩序下發生的」,而「如果一個犯罪行為因基於命令可得減刑,那麼對艾希曼最高刑罰的判決就難說得通」(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後記」)。艾希曼的律師以「國家行為」之名辯護艾希曼無罪,阿倫特則以「國家理性」作支持國家行為的論證:「國家理性」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基於「國家理性」的犯罪行為作為維持國家生存的緊急措施不受法律制裁(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後記」)。
艾希曼回憶他巡視集中營的經歷,「我掐了自己一把,以便確定這是真的、不是夢境。我甚至忘記測試致人以死要持續多長時間,而這正是米勒(Heinrich Müller,納粹帝國安全部部長)派我到那裡去的目的」 [16],他直言不諱,「我要誠實地告訴你們,我們攆走了一千萬猶太人,要是殺了他們我會更滿意,我會說,好,我們滅掉一個敵人」,「我可不是一個執行命令的一般人,要那樣我就是個白癡了,我自覺參與,我是個理想主義者」 [17]。
阿倫特的艾希曼沒有思想、不明所為、甚至全無深刻之惡這種誇張的一廂情願,令人驚異而不能不問,孰是孰非?要是阿倫特正確,那麼審判納粹的耶路撒冷法庭就錯了、那些批評她的人就錯了、法庭的證據和批評者援引的史料就錯了,艾希曼的行為和歷史也不真實了……然而常識而言,事實、史料、證據必要比口說心想靠譜。如果阿倫特錯了,爭議蜂起就不足為奇。
是肖勒姆口中阿倫特崇拜者的特點多少也適用於偶像阿倫特自身──「只不過是會擺弄字母」而「不用腦子思考」?還是她那挑釁的表達方式只為表現自己「不受束縛」的思想與雄辯?[18]大師級學者的觀察不是無的放矢,思想上的混亂必有其心智上的問題。
阿倫特的「行政屠殺」無罪性──作為「惡之平庸」的補充
常識而言,平庸,道德上不鼓勵但可以容忍;而惡行,則為道德禁止、被法律追究。常識而言,倫理上與社會中惡與平庸不同、也未必相通。落實「最終解決」 計畫遣送千萬生命去屠殺的艾希曼之惡行,難道可能是平庸的──平淡無奇、微不足道、司空見慣?──阿倫特「惡之平庸」的說法挑釁社會倫理,挑戰人們的心理極限。她在納粹艾希曼身上得出的惡之平庸的「教訓」,無論如何難以取信、難以服人,還是不得不求助「理論性」建構來支撐。
阿倫特提出納粹種族屠殺是人類歷史前所未知的「新型犯罪」,「新」在其作為國家犯罪的「行政屠殺」。而「行政屠殺」的本質據阿倫特,又是官僚主義的「無人機制」(rule of nobody)──無人管理、自動運行。官僚個人作為機制上的一個環節,在給定的位置實現預定的功能,誰在哪裡無關緊要(同注6,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後記」)。於是人成為非人,自動地完成功能,不明所以地犯罪──這是阿倫特所得的結論,「行政屠殺」一舉取消了極權體制中個人以及個人行為的責任。
「行政屠殺」的「無人機制」又為極權體制的結構性犯罪提供了「無罪性」說明,以官僚機制的功能取代從而取消犯罪,於是就抽掉了對犯罪行為道德譴責與法律追究的根據。不止耶路撒冷審判、紐倫堡、奧斯維辛審判中,艾希曼和所有納粹被告無不以清白的體制官僚自居、用忠於職守的「平庸」辯解,阿倫特與他們平行。
事實上,官僚機制為現代國家──極權的也罷、民主的也罷──的基本形式:確立目標、組織機構、制定功能,大至國家組織小到科室部門莫不如此。然而目標的設定、結構的建立和功能的實現都是人的行為而不是無人的機制,一概而論官僚主義非人化本質和官僚機制的「無人」運行,不符合實際。早年極權主義研究中阿倫特就曾提出說,蘇聯和德國的極權制度特性毋寧是由其組織形式而非意識形態決定的[19]。然而對艾希曼個案的研究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納粹官僚們的行為事實上是如何被納粹意識形態所支配[20]。同是官僚結構,納粹德國與聯邦德國從目標到功能處處不同,因為其官僚體制的基礎──它所從出的基本價值不同、國家的憲法不同,從而國家的地位、目的與功能處處不同。此外,便是同在納粹官僚體制中,有積極行使功能也有消極怠工甚至破壞其功能的官僚。如果官僚是人,官僚機制就不是無人機制。
阿倫特還有一個提法,說「新型犯罪」的納粹「行政屠殺」還有一「新」,即這種犯罪「全無任何外在的動因和可以辨認的目的」,以致超越一切道德維度。問題是,如果納粹罪行僅是官僚主義操作而與倫理、法律全然無關,它們豈不是可以完全不被譴責、根本不能審判了嗎? 阿倫特什麼「新型犯罪」、「行政屠殺」、「無人機制」的一套概念直接指向和挑戰耶路撒冷、廣而言之整個戰後納粹審判[21],顯而易見。
德國六十後vs. 阿倫特
辯護艾希曼,阿倫特寫了一本不薄的書;似是而非長篇大論,對納粹犯罪的態度曖昧不明。1964年,阿倫特到德國與菲斯特的廣播談話中,阿倫特大談年輕一代對納粹德國歷史真相沒有興趣。事實上,追究納粹時代發生了什麼、父輩做了什麼,在德國正是從1960年代逐漸開始,也是西德「六八學運」的一個重要動機。阿倫特的判斷至少表明,她對時代精神缺乏感覺。
下面援引一位德國1960後出生的德國人的一段話,清楚明白毫不含糊,使阿倫特「惡之平庸」的炫目頓時黯然。作者斐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1964年出生,與阿倫特為艾希曼辯護之書德文本同齡, 1946年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以反人類罪判處二十年徒刑的納粹巴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1907-74)是他的祖父,作為納粹維也納行政長官,他於1940到1945年間主持驅逐和遣送維也納猶太人。這是斐迪南關於他祖父文章中的一段話[22]:
「我祖父的行為完全不同。他的犯罪是有組織、有系統的,冷酷而精準。這些犯罪是在辦公桌上計畫的,有討論、有記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決策拍板。他說過,把猶太人趕出維也納是他對歐洲文化的貢獻。在這句話之後,一切心理分析都成為多餘;一個人的罪責如此之大,有時所有其它因素都可以忽略不計了。當然,那個國家本身就是犯罪的;但這並不能使他這樣的人免於罪責,因為是他們建造了這個國家。我祖父犯罪,不是觸犯了文明脆弱的表層;他的那些決定,不是出於魯莽、不是偶然、也非疏忽不周所致。今天在刑事審判中我們都會問,被告是否意識到自己的作為、是否理解自己的行為、是否能區分正義與不公。所有這些問題,對我祖父一案,可以很快得到解答。正因為如此,他的罪責尤其嚴重。他出身於一個幾百年來都承擔著社會責任的家族,他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整個世界都向他敞開;他原本可以輕易地選擇另外一種生活,他不是無辜獲罪。這些始終是最終給一個人量刑的前提」。
以常識和作為執業刑法律師對法律的理解與經驗,斐迪南確認祖父「不是無辜獲罪」,犯罪的國家不能免除罪犯個人的罪責,關閉了所有為納粹犯罪開脫的後門,包括阿倫特的「惡之平庸」。
阿倫特苛評猶太人
與對納粹「惡之平庸」的辯解平行,阿倫特對猶太人批評和指責構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的另一主題。對被種族滅絕的猶太人的苛評以致冷嘲,與對艾希曼同情的理解成鮮明對照,她備受非議不奇怪。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全書十六節,其中一半用於處置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然而其中大量篇幅是在談猶太人,談猶太人與迫害者的合作、他們對自身災難的重大責任。阿倫特的尖刻指責引發激烈爭論,也是出生於德國的著名猶太學者肖勒姆驚愕於阿倫特談論人們生死存亡的那種冷酷與「幸災樂禍」的口吻,直言「毫無心肝」。
一、阿倫特論猶太人自我毀滅的罪責
怎麼看待對阿倫特的批評?首先要看她說了些什麼,怎麼說的。關於猶太人自己對本族被滅絕的責任,她談了很多,這裡僅擇要摘錄一、二。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4年英文增訂版首頁篇幅不長的「致讀者」一文中,阿倫特對納粹的種族滅絕即表質疑,「『最終解決』的猶太人犧牲者總數──四百五十萬到六百萬之間──只是猜測,從未得到證實,具體到每個國家猶太受害者的數字也是如此」[23] 。在「法庭」(The House of Justice)一節中,她指責法庭只是審訊和判決,而對那些在她看來遠為重要的問題不聞不問;例如:「為什麼是猶太人」和「為什麼是德國人」的問題,「猶太人如何因為其領袖的通敵而走向毀滅」,「為什麼他們如羔羊般走向死亡」等等。然而阿倫特首先需要說明,為什麼她這些問題對於法庭應該比審判艾希曼更重要?畢竟,法庭的任務是審判艾希曼及其在納粹種族滅絕中的犯罪,而猶太人是這一犯罪的犧牲者。
「後記」中阿倫特說她這種批評是對猶太歷史的反思,針對「最終解決「災難中猶太民族的表現。具體地,阿倫特言之鑿鑿:「柏林對猶太人最後的圍捕,沒有行政和警察措施上猶太人的協助無法實現,如我已經提到的,那完全是猶太警察完成的。……一樣的現象在更大的範圍上,也適於那些被送到波蘭被處死的猶太人」。阿倫特一概而論:「凡猶太人生活和有公認領袖的地方,那些領袖均幾無例外地出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這樣或那樣地與納粹合作。總體的真相是,如果猶太人沒有組織群龍無首,可能會一團混亂、災難重重,但受難者總數一定不會高達四百五十萬到六百萬之眾。」
更有阿倫特最張揚的激憤:「在滅絕族人中,猶太領袖的作用毫無疑問是黑暗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24],最強烈的自以為是:「始於本族的不公,自然比外族加諸的不公更令我義憤[25]。」
自然誰都有權選擇他對什麼更義憤,但表達的前提對任何人皆無不同:他的義憤必須是有根據的,而他的根據必須是真實的。阿倫特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表明她關於猶太人「黑暗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的陳述是確實的。
二、第三者旁觀阿倫特
作為第三者的觀察,《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86年德文本的「蒙森序」提供了一個與阿倫特議論值得注意的對照。德國人、保守自由主義者和德國當代史學者的身分,以及在戰後四十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二十年和阿倫特離世十年之後的距離,奠定了蒙森觀察的資格和觀察價值。
對於阿倫特,「耶路撒冷審判的歷史意義,在於揭示了『在怎樣駭人的程度上猶太人參與了協助組織自身的滅亡』」,以致「沒有猶太人組織領導人的合作,『最終解決』不可能達到那樣的規模」。蒙森態度明確地指出,這種說法「被納粹種族滅絕的倖存者指為冷酷無情與狂妄傲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6] ;他直言不諱,阿倫特那種尖刻嘲諷的口吻,對於她所談論的題目深刻的悲劇性失了分寸。
作為納粹德國史專家,蒙森確認「猶太居民委員會、德國猶太人聯合會和黨衛軍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強制合作」。全國性的猶太人聯合會(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本身就是納粹當局建立和支配的,直接隸屬納粹帝國安全部(RSHA)和秘密警察,猶太人必須加入;基層還有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at)管制猶太人,委員由納粹當局指定。蒙森繼而提問,阿倫特激烈指責猶太領袖與納粹合作,為什麼沒有對合作的強制性做出說明?阿倫特責備猶太人缺少反抗意志,甚至有「沒有反抗的可能性還有不作為的可能性,不合作並不需要成為英雄」的冷嘲[27],為什麼不追究猶太人缺乏反抗意志背後的原因?
不僅對經歷過納粹時代的德國人蒙森、對後來人如筆者──以人之為人的平常心智,都感到難以理解和接受阿倫特的猶太「批評」和結論。她的問題出在哪裡,智力上,還是道德上?
阿倫特否定國際納粹審判
此非聳人聽聞,實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另一重大主題。阿倫特對於國際納粹審判的挑戰,像她的猶太批評一樣隨意、極端而轟動。
對於耶路撒冷審判,阿倫特近乎否定:一方面她質疑以色列究竟是否有權審判艾希曼,另一方面她辯護艾希曼為國家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其結果是否定對艾希曼的審判。至於把艾希曼審判表述為受害種族的復仇、以色列宣揚其合法性的政治秀,則是阿倫特耶路撒冷批評的副產品──她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建國。
在沒有遇見這些文字之前,對於阿倫特對納粹審判竟持一種基本否定的態度,筆者不曾料想於萬一;即使面對她的文字,仍然難以置信。
一、劫持艾希曼和以色列審判
阿倫特不止一次主張,耶路撒冷審判和紐倫堡審判一樣,都是戰勝者的審判──這個說法筆者不陌生,德國的新老納始終是這樣看待納粹審判的,出於阿倫特之口,卻是意外。站在勝利者一邊,通過非法劫持而至審判,這是阿倫特質疑耶路撒冷審判司法正當性批評的入門。
劫持之為艾希曼審判的障礙,自不待言;雖然如此,以色列劫持艾希曼與耶路撒冷審判艾希曼仍然是兩件彼此分開而且不同的事情。劫持艾希曼違背國際慣例並侵犯阿根廷國家主權,不言而喻。此一以阿爭端,後經聯合國安理會介入以及透過外交途徑而平息,阿根廷放棄了引渡艾希曼的要求。劫持的障礙消除後,就面臨誰來審判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確定不以劫持與否為前提,即劫持不能否決審判。根據國際法屬地原則(territoriality principle),一個主權國家可在它領土之內行使司法權。西德無疑對艾希曼擁有審判權,因為艾希曼作為德國人,他的犯罪行為是在德國主權和領土上發生的。但是德國不要求引渡和審判艾希曼。阿根廷因放棄引渡也排除在外,況且那裡十五年的刑法追訴期已過。當時也沒有現成的國際司法機構可以審判艾希曼,雖有海牙國際法庭,但是作為聯合國機構,只限於審理成員國之間的法律糾紛(國際刑事法庭直到2002年才產生),於是國際社會接受了由以色列來審判艾希曼。對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86年德文增訂版蒙森序開篇即有說明[28]。
此外,劫持艾希曼實際上有它不得已的原因和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艾希曼匿藏阿根廷的確切資訊,西德至遲至1956年、甚至早於1952年就已確切掌握,但根本不準備引渡和審判艾希曼,這個立場未因他的劫持而改變,連艾希曼的辯護律師都是由以色列付費,聯邦德國不想和他發生關係。可以說,若不是劫持就不會有艾希曼審判,納粹「最終解決」的猶太人種族滅絕真相至今還會藏在在黑暗中。把艾希曼匿藏消息傳遞給以色列的是法蘭克福檢察總長鮑爾,1965年德國奧斯維辛審判之父。審判結束兩週後,1968年7月1日,鮑爾被發現死於住所的浴缸,享年不足六十五歲。和阿倫特一樣,鮑爾也是猶太人和納粹德國的逃亡者──這無關緊要;和阿倫特不同,鮑爾視罪惡為罪惡而非「平庸」,為審判罪惡重建正義,他竭盡努力、付出了生命。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阿倫特因「惡之平庸」聲名鵲起;鮑爾留下奧斯維辛審判,讓後世永遠銘記、拒絕並阻止反人類的罪惡。
二、阿倫特挑戰納粹審判的司法正當性
不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知道阿倫特奚落、指責和否定耶路撒冷直至紐倫堡審判;不讀阿倫特的文字,便不瞭解她對納粹犯罪的「理性」護航。而這,又超出了常情、常理、常人通常可以想像、理解和接受的界限。白紙黑字無法迴避,阿倫特的中文論者必須面對、思索和修正先入為主的盲目之見。
二‧一、質疑以色列的審判權
阿倫特的批評基本上否定了耶路撒冷的司法權及其審判的法律正當性,她認為耶路撒冷審判「侵犯了司法正義」,與紐倫以及其它歐洲國家的戰後審判同為敗筆。
首先她批評耶路撒冷審判違背國際公法中禁止回溯原則和屬地原則。禁止回溯原則禁止將現行法律應用於既往,阿倫特提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審判的行為發生之時,以色列尚未存在;且艾希曼的行為不是發生在以色列領土,耶路撒冷審判因此又違背了屬地原則。屬地原則禁止一個國家對領土以外行使司法權,允許的例外為援引其它原則,例如被動人格原則或司法普適性原則。當境外罪犯為本國公民或本國公民國民為境外犯罪受害者的情況下,被動人格原則允許主權國家延伸它的刑法權到境外;為納粹種族滅絕受害者的猶太國民,以色列於是有權審判艾希曼。而司法權普適性原則,允許國家或國際組織不受罪犯或受害人個體屬性、罪行發生地域及其所屬國家法律限制,對於那些針對人類全體的犯罪行使司法審判權。
因此,司法普適性不僅是耶路撒冷,而且是紐倫堡審判所本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國際刑法原則。倫敦憲章授權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二戰一切反人類罪,包含種族滅絕罪,無論它們是否違反罪行發生所在國家的法律。阿倫特拒絕耶路撒冷援用司法普適性原則[29],無異對耶路撒冷審判合法性釜底抽薪。她甚至指責耶路撒冷審判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是出於猶太人作為受害者報復心理和復仇[30]。阿倫特重複艾希曼的辯護律師,說猶太國家審理對猶太人的罪犯違背了保障法律公正的迴避原則(涉入案情者要迴避司法審理)。此處,阿倫特忽略艾希曼之罪不是艾希曼個人對猶太人個人的犯罪,而是種族滅絕的反人類罪,以色列因司法普適性原則而行使司法權。彼處,阿倫特又強調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是反人類罪,堅持反人類罪就不能由以色列而一定要國際法庭審判。記者阿倫特女士的論斷,經常這樣因地制宜。
二‧二、否認紐倫堡審判的司法正當性
戰後的其它納粹審判,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均援紐倫堡審判為先例。阿倫特對耶路撒冷審判的否定無可避免直指紐倫堡審判,她說「尤其必須承認,耶路撒冷審判的失敗無論是在性質上還是在程度上,都不比紐倫堡或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戰後審判更嚴重」,明言 「耶路撒冷法庭的一些失敗恰恰是由於太緊跟紐倫堡審判的先例了[31] 」。
倫敦憲章作為紐倫堡審判的法律基礎
二戰結束之前,1943年10月成立的聯合國戰爭犯罪委員會(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曾提出戰後審判戰爭犯罪的建議,成為1945年《倫敦憲章》(London 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的依據。倫敦憲章確立盟國美英法俄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德國戰爭犯罪,成為紐倫堡審判的法律基礎。《倫敦憲章》宣布,國際軍事法庭審理軸心國的戰爭犯罪、反和平罪和反人類罪罪行(法規第六條),審理罪行不局限於某一地區、也不論罪犯為個人還是組織成員(協定第一條),尤其明確規定「被告公職──無論是作為國家首腦還是政府官員,不成為被告免罪和減刑的根據」(法規第七條),換句話說,依據1945年《倫敦憲章》,阿倫特1963年想出來的「行政犯罪」,不構成對艾希曼審判的障礙和免罪的根據。
1946年10月1日,紐倫堡審判宣判十二名德國納粹首犯死刑,2016年紐倫堡審判七十周年,德國的紀念活動一致指出,紐倫堡法庭審判反人類罪,是現代國際刑法的里程碑。沒有紐倫堡審判就不會有人權宣言,不會有本世紀設立的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以及對一系列反人類罪的國際審判。這一切都是《倫敦憲章》原則的繼續,當年面對納粹國際審判,阿倫特明確站在民族國家司法主權──具體說納粹德國的司法主權的立場,反對司法普適性原則。
耶路撒冷審判的法律根據:
以紐倫堡法庭的模式,1950年8月9日以色列通過了《納粹和納粹合作者(懲處)法》(NNCL:Nazis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 5710-1950 ),奠定了日後耶路撒冷審判的法律基礎。 NNCL以1945年的倫敦法規和1936年的刑法法典(CCO:Criminal Code Ordinance[32])為依據,規定審理反猶與反人類的刑事犯罪與戰爭犯罪。否認耶路撒冷的審判權,必然導致顛覆紐倫堡審判的司法正當性。
阿倫特vs. 司法普適性原則和納粹反人類罪:
阿倫特反對耶路撒冷法庭以紐倫堡審判為例援用司法普適性原則,說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起訴「不是因為他對人類犯罪……而是他對猶太民族犯罪」[33]。艾希曼的犯罪行為顯然不在兩個個體之間,阿倫特是要求審判以納粹對全體人類犯罪為條件嗎?
阿倫特書中曾援引紐倫堡審判首席檢察官泰勒(Telford Taylor)討論反人類罪,然而在被援引的那篇文章「艾希曼一案的普遍問題」中泰勒明確指出,「宣稱殺害猶太人是對猶太人犯罪的危險含義在於說它不是對非猶太人的犯罪……紐倫堡審判的基礎是,針對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暴行一樣是違背國際法的犯罪……以受害者宗教或民族的名義而不是罪行的性質定義犯罪,完全背離時代需要和現代法律趨勢」[34]。
阿倫特所謂納粹犯罪的「國家行為」解
這不是言過其實,是阿倫特對艾希曼為國家的犯罪行為的又一辯解。
當作純思辨,對於「惡之平庸」未必能夠嚴肅地爭論,有無思想且是否平庸,並無公認的標準可以衡量、有實據能夠驗證。對耶路撒冷司法的質疑卻有一箭雙雕之功,抽掉審判的合法性根據無異辯護被告無罪。阿倫特左手以「行政屠殺」定義極權國家的體制性犯罪為「無人機制」,從而解脫了作為犯罪機制一環的個人及其行為的罪責;右手祭出「國家理性」,繼而取消了對納粹國家體制性犯罪法律制裁的根據。阿倫特本人文字直接而明確,只需援引而不必解釋。
對於艾希曼的犯罪阿倫特確強調「無可否認,這些罪行是在一個『合法』的制度下發生的」[35],換句話說,就是艾希曼的行為不犯法。這個說法與艾希曼辯護律師如出一轍,如「被告」一節她自己對艾希曼辯護律師瑟威舍斯(Robert Servatius)的轉述:「在納粹的法律之下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他被起訴的不是罪行而是『國家行為』,對於國家行為其他國家無權審判」[36]。阿倫特附和這種說法,「『國家行為』理論主張司法上一主權國家不能居於另一主權國家之上」; 她也看到「如果接受這個論點,甚至對唯一不能逃避責任的希特勒都不能追究法律責任,而這侵犯了基本的正義感」;但是她堅持「實踐上行不通的卻不是理論上也不成立」,具體而言即「通常的託辭—─第三帝國期間德國是被一犯罪團夥統治、它不能享有主權與平等,也沒有什麼用。……人人都知道,犯罪團夥的比喻只在一個有限的意義上甚至根本就不成立」[37];說白了就是,納粹德國是一個與其他國家無不同的主權國家。
阿倫特骨鯁在喉的是什麼呢?是想讓讀者明白,納粹德國也不能歸約為犯罪團夥,對納粹犯罪作為主權國家的「國家行為」不可審判?須知,主權國家司法平等是國際法原則,而「國家行為」不是,它們分屬不同範疇;從主權國家司法平等導不出「國家行為」免於刑責的結論。
進一步,阿倫特祭出「國家理性」以證納粹「國家行為」可以無罪:「根據國家理性,對國家生活及其法律負有責任的國家行為不受支配公民個人行為同樣的規則制約。法律制止暴力和戰爭,同時承認以暴力手段維護法律的必要。同理,為維護國家自身及其法律的存在,政府也會被迫採取通常認為是犯罪的行為。」[38] 「國家理性訴諸必要性,以國家之名的犯罪,是作為迫于現實政治需要的緊急措施,用以維護政權及其法律制度之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在正常的政治法律制度中,這種犯罪作為規則的例外不受法律制裁,因為國家處於危急之中,外在政治實體無權剝奪它的生存或者決定它如何維持自己的生存」[39]。結論於是無可避免:如果「國家理性」允許國家行為犯罪而不犯法,對執行納粹國家行為「行政屠殺」的艾希曼就不能懲罰。不就是國家至上麼?──德國思想傳統中最災難性的部分,抱琵琶半遮面究竟遮掩不住。
應當不難理解,國家內部,憲法在上制約「國家理性」;國際間,「國家理性」[40]並非國際法規則,不成國家行為是否受法律制裁的根據。即使在最嚴肅的論證中,如她的許多支持者和批評者指出的,阿倫特也不憚隨意,甚至是必須避免和絕不容許的隨意。
阿倫特的「惡之平庸」為什麼走紅?
上述種種對中文讀者也許是一個震動。在「惡之平庸」的原生地西方,這是確實發生過、白紙黑字有記載的事情。只是在這個詞的中文在「拿來」過程中失真了,給了受眾一個假像。真相不難瞭解,簡要概括的西文辭書上都有介紹,沿索引的線索也可以深入;何況在一個網路時代,詞條輸進去,資料不怕找不到,只怕應付不了。偷工減料偷懶的「拿來」不必說是失職──有負受眾也愧對原創,這樣「拿來」出來的東西不必說沒有價值。
讀者也許會反問,對「惡之平庸」不是也有認可與好評嗎?阿倫特在西方不也是很有名嗎?是的。因此在動筆之前,筆者也閱讀瞭解這個面向。讀到那些對阿倫特「惡之平庸」的肯定,鮮少看到又新材料確證阿倫特的說法或深入的分析論證,大多停留在為阿倫特背書。
觀察這個概念以及阿倫特本人在德國—─這個特殊境遇──所得的承認,對於瞭解戰後德國的歷史不無意義。阿倫特及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德國頗獲好評,是正逢其時,合了德國那個時候的社會氣圍:忘掉過去,對身後的「過去」三緘其口或避重就輕。面對對納粹罪犯的審判和追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惡之平庸」出自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阿倫特之口,可遇而不可求。奧斯維辛審判開庭的時候,法庭前的警衛對進入受審的納粹被告行禮致敬,有圖有真相,那是1963年底。
並且不止於戰後德國當時的社會氣圍和時代精神,還有國家機構在身後。戰後不是民主政府了嗎?—─不錯。納粹國家不再,但是納粹國家的雇員聯邦德國的新政府中基本留下,這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影響了政府政策、司法和行政。最近(2016)公佈的德國司法部《羅斯堡文件—聯邦德國司法部和納粹時代》(Die Akte Rosenburg – Das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die NS-Zeit)專案研究結果表明,1949~1973年間聯邦德國司法部170名高級官員中有77%即一百三十四人有納粹背景,其中九十人為納粹黨員, 三十四人為衝鋒隊員,有15%直接來自納粹司法部。
1960年代初期奧斯維辛審判阻力重重步履維艱,主持和推動奧斯維辛審判的黑森州最高檢察官鮑爾在給朋友的私信中時有流露,「身在司法界如同置身於流亡」,「一走出辦公室,就踏上一個充滿敵意的外國」。阻礙和壓力從何而來?來自國家──戰後的聯邦德國政府。以總理府為例,聯邦德國初建的1953-1963十年間,掌聯邦總理阿登納總理府事務十年之久的辦公廳主任即前納粹司法部官員、參與制定和負責解釋臭名昭著的紐倫堡種族法的格羅布卡(Hans Josef Maria Globke),他的職權包括建議部長任命人選,專設機制監視他們的忠誠度,建議並參謀總理阿登納的重要決定。鮑爾在奧斯維辛審判結束不明身亡後被冷藏了五十年,2015年德國發行了一部故事片描述這位追訴納粹犯罪司法人白年代的工作遭遇,片名直曰《國家對著弗裡茨‧鮑爾》(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同年英文拷貝上市,題名《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國家」和「對著」的關鍵字都消失,是這樣的意義組合太刺目?然而事實確實如此,恰恰是德語影片要說的故事。可惜。
那個最終在耶路撒冷受審的納粹要犯艾希曼戰後初期遭遇如何呢?1945年艾希曼化名被俘,1946年收買一被俘黨衛軍逃出,從奧地利再化名輾轉到北德呂訥堡(Lüneburg)附近落腳隱藏下來一直到1950年。其間得天主教會幫助化名瑞卡多‧克萊門特(Ricardo Klement)取得進入阿根廷的許可、獲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發放的人道護照(humanitarian passport ),在教會人士幫助下取道義大利終合法移民阿根廷,受雇當地賓士汽車公司維生。那個時候,社會氣氛並不怎麼敵對納粹犯罪。《圖片報》2011年撰文披露,艾希曼匿藏阿根廷的資料聯邦情報局1952年檔中有詳細記載例如化名住址等等;如果沒有鮑爾檢察官的鍥而不捨,納粹艾希曼或能在阿根廷「平庸」以終。
從未雨綢繆匿名潛藏到千方百計逃出德國,可見艾希曼對一己犯罪的自覺,絕不平庸糊塗。紐倫堡審判 中,被告奧斯維辛典獄長Rudolf Höss對於艾希曼與此相關的罪行亦有證詞。於是,要洗刷納粹艾希曼,就要把他的罪感與逃匿歸咎於對納粹的法律追訴、歸咎於紐倫堡審判、歸咎於追訴納粹犯罪的大檢察官鮑爾和猶太人,這些也確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的論題、以及該書初期在德國取得積極反響的原因所在。
蒙森序代結束語
簡而言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阿倫特提出一個備受爭議的說法「惡之平庸」,質疑實施滅絕猶太種族「最後解決」計畫的納粹罪犯艾希曼的罪與惡和耶路撒冷和以及紐倫堡審判的正當性,一鳴驚人猶太人在種族滅絕中自我罪責為「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本文介紹了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的重要論點以及西文相關爭論的大致,希望有助於降溫中文世界盲目無知的「平庸之惡」熱。
1986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問世二十年再版十四次之後,以德國當代史家蒙森序增訂再版。一個不能更好的選擇,一位享譽國際的學者,而且是當代納粹德國歷史的專家,這個序自有它的分量;如今三十年又過,蒙森序價值依舊。為中文讀者不錯失蒙森以史實為證以學術為本對於阿倫特其書求實的觀察、嚴謹的分析、公允的批評,本文引蒙森序以為結束。
阿倫特的公共言論長於譏諷、不避激化,即使對於猶太人種族滅絕那樣嚴肅敏感的論題也不例外,「惡之平庸」引發激烈爭議當不意外;而阿倫特「沒有充分估計到她艾希曼的文章引發爭論的規模和尖銳程度」[41],序者蒙森直言這才是需要解釋的。
身為經歷過納粹時代的德國人蒙森指出,對猶太人工業化的屠殺當時一般人可能不瞭解,但是「毫無疑問,德國人知道,那些都是公開遣送的猶太人必面臨殘酷的命運」[42]。阿倫特于艾希曼犯罪行為發現「平庸」的地方,歷史學家蒙森指出「納粹制度即建立於對令人不適意或兇殘現象集體排斥的機制,艾希曼是這一機制的典型,用無關緊要的美德(例如服從、勤勉、盡職,筆者注()論證屠殺的正當性)[43],而「官僚精英的道德冷漠,遠在1933年之前」[44]。
在阿倫特飽受爭議的論題及其嘲諷挑釁的議論方式背後,蒙森注意到其中她特殊的個人因素: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她「德國—猶太人身份認同上的困境」、「主觀上明確的猶太人意識與以觀念論和浪漫主義為特徵的德國文化傳統無法割捨的連繫之間的緊張」,還有「她對海德格從未真正熄滅的青年時代的戀情」,而出身同化了的猶太人中產階級家庭,本質上「阿倫特始終保持為深入骨髓的布爾喬亞」。[45]這些都不容忽視地參與影響了她對納粹艾希曼的判斷、對猶太人和戰後納粹審判的態度及其令人不無保留的表達方式。
涉及阿倫特的論題本身蒙森指出,例如關於「最終解決」阿倫特的解釋漏洞不少,有的地方不自洽,資料來源上缺乏足夠的證據」[46]。
從思想理論上觀察依蒙森,阿倫特「始終在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及其精英和非政治姿態的影響之下……她理論著作狹義政治哲學的局限明顯地表現為排除社會問題在外」[47]。論說方式上,「她聞名遐邇的知性的吸引力在於其獨特的把彼此顯然不相容的東西辯證地連接在一起的論辯」,「阿倫特典型的辯證法論證方式可回溯到她與早期存在主義哲學的密切接觸。反歷史的基本特徵……也貫穿於阿倫特的所有哲學以及報刊文章中。她因此能夠打破實證主義的專業化傳統,把種種非常不同的時代體驗以啟蒙思想的名義知性地強制糾集在一起,以一種萬有的結構展示她令人著迷的見解,自然也不免生拉硬扯的構造」[48],至於思想方法,蒙森一再直接而明確,「基本上,她沒有方法,而是用印象派的移情把不同物件捏合到一個以本體論統合的整體之下」。
2015年3月初稿,2016年11月修訂
[1] 見《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tmagazine.com/culture/20130604/c04arendt/zh-hant/,原出Fred Kaplan: “The Woman Who Saw Banality in Evil”, NYTime, May 24. 2013。
[2] 見《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cn.tmagazine.com/books/20140918/t18eichmann/zh-hant/,原出Jennifer Schuessler: Book Portrays Eichmann as Evil, but Not Banal, NYTime, Sep 3. 2014。
[3] 見蒙森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1986年增訂版(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Piper,2003,“Hans Mommsen: Hannah Arendt und der Prozeß gegen Adolf Eichmann”〈漢娜‧阿倫特和艾希曼審判〉)。
[4] 見〈「文革」的雙重性:國家之罪與「平庸之惡」〉一文中片語「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Evil of banality)』」,可證「平庸之惡」為阿倫特「banality of evil」的誤讀。
[5] 關於德國奧斯維辛審判首席檢察官鮑爾與耶路撒冷艾希曼審判的關係,見還學文〈從清算到重建──看戰後德國面對歷史遺產〉,《財新新世紀週刊》2014年第6期;另見德文紀錄片《弗裡茨‧鮑爾── 分期死亡》(Ilona Zioks: Fritz Bauer – Tod auf Raten,2010)。
[6]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4年英文增訂版,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The Viking Press, 1964。
[7] 關於戰後西德去納粹化狀況,見還學文〈盟軍佔領與戰後西德〉,《財新中國改革》2014年第3期。
[8] 見薛巍〈漢娜‧阿倫特論惡的平庸性〉,三聯生活週刊,2011年9月23日。
[9] 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後記」(Postscript),“This book, then, does not deal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est disaster that ever befell the Jewish people, nor is it an account of totalitarianism, or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in the time of the Third Reich, nor is it, finally and least of all, a theoretical treatise on the nature of evil. The focus of every trial is upon the person of the defendant, a man of flesh and blood with an individual history, with an always unique set of qualities, peculiarities, behavior patterns, and circumstances.”
[10] 見黃默(Mab Huang)“Hannah Arendt on Banality of Evil”, 東吳政治學報,2006,第二十三期,p.10,引〈雅斯貝爾斯1961年6月8日致阿倫特〉(Elis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p.520)。
[11] 同注10,見黃默(Mab Huang): “Hannah Arendt on Banality of Evil”,東吳政治學報/2006/第二十三期,p.13, “Some years ago, reporting the trial of Eichmann in Jerusalem, I spoke of ‘the Banality of evil’and meant with this no theory or doctrine but something quite factual, the phenomenon of evil deeds,…”(Arendt 1971 in Richard Bernstein: Radical Evil: A Philosophical Interrogation, Co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219)
[12] 廣播談話〈漢娜‧阿倫特與約阿希姆‧菲斯特對談〉(Hannah Arendt im Gespräch mit Joachim Fest, 09.Nov.196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F_UvHhbZIA)。原文見〈漢娜‧阿倫特與約阿希姆‧菲斯特對談,1964年廣播談話〉(Hannah Arendt im Gespräch mit Joachim Fest Eine Rundfunksendung aus dem Jahr 1964, Hg. Ursula Ludz und Thomas Wild (Vorbemerkung u. Anmerkungen), Okt. 2007),並收入《漢娜‧阿倫特與約阿希姆‧菲斯特 艾希曼令人憤怒的愚蠢,對話與通信》(Hannah Arendt & Joachim Fest. Eichmann war von empörender Dummheit. Gespräche und Briefe, 2011)一書。
[13] 同注12,並見http://www.hannaharendt.net/index.php/han/article/view/114/194:“Nun, ein Missverständnis ist das Folgende: Man hat geglaubt, was banal ist, ist auch alltäglich. Nun, ich glaubte … Ich habe es so nicht gemeint. Ich habe keineswegs gemeint: der Eichmann sitzt in uns, jeder von uns hat den Eichmann und weiß der Deibel was. Nichts dergleichen! Ich kann mir sehr gut vorstellen, dass ich mit jemandem rede, und [der] mir etwas sagt, was ich noch nie gehört habe, was keineswegs alltäglich ist. Und ich sage: `Das ist äußerst banal.´ Oder ich sage: `Das ist minderwertig.´ In diesem Sinne habe ich es gemeint.”
[14] 例如徐賁〈平庸的邪惡和個人在專制制度下的道德責任〉(2002)可為這類阿倫特「平庸之惡」後理論建構之一例,作者為阿倫特的後理論建構即從「平庸的邪惡」這一誤譯、誤解開始的。至於將艾希曼(Eichmann)誤譯為「艾克曼」更使文章的嚴肅性大打折扣。
[15] 同注6,「被告」(The Accused), “The defense would apparently have preferred him to plead not guilty on the grounds that under the then existing Nazi legal system he had not done anything wrong, that what he was accused of were not crimes but “acts of state,” over which no other state has jurisdiction (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 that it had been his duty to obey and that, in Servatius’ words, he had committed acts “for which you are decorated if you win and go to the gallows if you lose” ,艾希曼的律師Robert Servatius在紐倫堡審判中也為納粹戰犯被告辯護。
[16] 判決之前,艾希曼將一疊手稿交給法庭希望與判決同時公布,以給世人以另一艾希曼的形象。鑒於三十次庭審筆錄已公之於眾,法庭未准。此手稿於1980年解密公布,時見援引,2000年首次以《艾希曼回憶錄》形式出版。
[17] 1956年薩森(Willem Sassen, 1918-2001,荷蘭前納粹記者)開始對艾希曼採訪,有文字稿經艾希曼本人修訂,準備出書反駁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1960年5月23日艾希曼被劫持到耶路撒冷宣布逮捕後,薩森將部分採訪副本賣給德國《明鏡》、《明星》週刊和美國《生活》(Life)雜誌發表。經過各自不同的途徑,耶路撒冷法庭獲得很少一部分採訪錄音副本、奧斯維辛審判的法蘭克福首席檢察官鮑爾(Fritz Bauer)得到完整的文字副本,艾希曼的律師後將他掌握的部分賣給西德國家檔案館,艾希曼的弟弟羅伯特(Robert)盜走一部分,薩森後將手中剩餘的文字原件和採訪錄音交給家屬,這一部分後也輾轉到西德國家檔案館。但是整個採訪始終沒有完整出版。關於這些,斯坦尼思女士有研究發表。
[18] 同注3,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蒙森序」。
[19] 見漢克(Klaus-Dietmar Henke,1947-)〈惡──不過是平庸的?〉(Das Böse – Nur Banal?)一文,發表於《明鏡週刊》(Der Spiegel),2001年9月3日。漢克為德國當代史教授,1997-2001年任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研究所(HAIT)所長。
[20] 見蔡薩拉尼(David Cesarani,1956-)的艾希曼傳記《成為艾希曼》(Becoming Eichmann,2005),蔡薩拉尼為英國歷史學家,專門研究猶太及對其種族大屠殺的歷史。
[21] 同注3,參見《惡之平庸》德文本「蒙森序」,“Die Einzigartigkeit des `Holocaust´ erblickte sie in dem Fehlen jeglicher moralischer Dimensionen, damit der ausschließlich technokratischen Natur des Vorgangs. Sie überforderte mit dieser Konsequenz jedoch die Möglichkeiten des Gerichtshofs, und dies hätte auch für jedes andere Gericht gegolten”, p.23。
[22] 原文見《明鏡週刊》2011年第36期〈你就是你〉(Ferdinand von Schirach: “Du bist, wer du bist”, Der Spiegel,2011年3月6日)。中譯〈你,就是你自己──為什麼我無法回答那些關於我祖父的問題〉,見《新世紀週刊文化版》2015年第9期。
[23] 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致讀者」(Note to the Reader),“Thus the total number of Jewish victims of the Final Solution is a guess – between four and a half and six million – that has never been verified,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totals for each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24] 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萬湖會議」(The Wannsee Conference, or Pontius Pilate),“To a Jew this role of the Jewish leaders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own people is undoubtedly the darkest chapter of the whole dark story”。
[25] 援引自《肖勒姆通信》(Gerhard ScholemII, p.100),阿倫特於1963年7月20日致肖勒姆信。
[26] 同注3,隨後幾處直接或間接援引蒙森序。
[27] 見《肖勒姆通信》(Gerhard Scholem II , p.100),阿倫特1963年7月20日致肖勒姆。
[28] 同注3,序中注①和②表明他援引了以色列作家Moshe Perlman(1911-1986)《逮捕艾希曼》(Die Festnahme des Adolf Eichmann)書中的論證,並說明此論證為阿倫特拒絕。
[29] 同注6,「跋」(Epilogue),“the court, to justify its competence, would have needed to invoke neither the principle of passive personality… nor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Both theories, … actually blurred the issues and obscured the obvious similarity between the Jerusalem trial and the trials that had preceded it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special legislation had likewise been enacted to ensure the punishment of the Nazis or their collaborators.”
[30] 同注6,「跋」(Epilogue),“that it was established no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justice but to still the victims’ desire for and, perhaps, right to vengeance.”
[31] 同注6,「跋」(Epilogue),“It must be admitted furthermore that their failures were neither in kind nor in degree greater than the failures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or the Successor trials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contrary, part of the failure of the Jerusalem court was due to its all too eager adherence to the Nuremberg precedent wherever possible.”
[32] “Criminal Code Ordinance 1936”究竟為何,以色列最高法院未予解釋,直到以後的年代CCO來源問題仍然懸而未決,見Norman Abrams:Interpreting the Criminal code Ordinance,1936 – The untapped Well》 (1972)。
[33] 同注6,「跋」(Epilogue),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t was said, was applicable becaus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re similar to the old crime of piracy, … Eichmann, however, was accused chiefly of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and his capture, which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was meant to excuse, was certainly not due to his also having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but exclusively to his role in 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Jewish problem. ”
[34] 見《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61年1月22日〈艾希曼一案的普遍問題〉
(Large Questions in the Eichmann case), “To proscribe the murder of Jews as a crime against Jews carries the dangerous implication that it is not a crime against non Jews….Nuremberg was based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atrocities against Jews and non Jews are equally crimes against world laws ….To define a crime in terms of the religion or nationality of the victim, instead of the nature of the criminal act, is wholly out of keeping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trend of modern law. ”
[35] 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後記」(Postscript),“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crimes undeniably took place within a‘legal’order.”
[36] 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被告」(The Accused), “The defense would apparently have preferred him to plead not guilty on the grounds that under the then existing Nazi legal system he had not done anything wrong, that what he was accused of were not crimes but “acts of state,” over which no other state has jurisdiction”。
[37] 這一段中引言出處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後記」(postscript), “The theory of the act of state is based on the argument that one sovereign state may not sit in judgment upon another, … if it were accepted, even Hitler, the only one who was really responsible in the full sense, could not have been brought to account – a state of affairs which would have violated the most elementary sense of justice. However, an argument that stands no chance on the practical plane has not necessarily been demolished on the theoretical one. The usual evasions – that Germany at the time of the Third Reich was dominated by a gang of criminals to whom sovereignty and parity cannot very well be ascribed – were hardly useful. … everyone knows that the analogy with a gang of criminals is applicable only to such a limited extent that it is not really applicable at all”。
[38] 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後記」(postscript), “Perhaps we can approach somewhat closer to the matter if we realize that back of the concept of act of state stands the theory of raison d’état. According to that theory, the actions of the stat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life of the country and thus also for the laws obtaining in it, are not subject to the same rules as the acts of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Just as the rule of law, although devised to eliminate violence and 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 always stands in need of the instruments of violence in order to assure its own existence, so a government may find itself compelled to commit actions that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crimes in order to assure its own survival and the survival of lawfulness.”
[39] 同注6,見《惡之平庸》英文本「後記」(postscript), “Raison d’état appeals – rightly or wrongly, as the case may be – to necessity and the state crimes committed in its name (…) are considered emergency measures, concessions made to the stringencies of Realpolitik, in order to preserve power and thus assure the continuance of the existing legal order as a whole. In a normal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such crimes occur a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and are not subject to legal penalty (…)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itself is at stake, and no outside political entity has the right to deny a state its existence or prescribe how it is to preserve it.”
[40] 「國家理性」作為國際關係中一個政治觀念,主張以國家利益為國家行為最高準則—即使不擇手段、違背道德和法律。此說十六世紀中期發軔於馬基雅維利,對內以強調世俗國家獨立於宗教與倫理,對外以國家利益至上主導國際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歷批評而變化,尤其是涉及到國家權力與法律的關係;當代已為「國家利益」觀念取代。
[41] 同注3,蒙森序,”Gleichwohl ist es erklärungsbedürftig, daß Hannah Arendt das Ausmaß und die Schärfe der Polemik, die ihr nach den Eichmann-Artikeln entgegenschlug, nicht hinreichend antizipiert”, p.33.
[42] 同注3蒙森序,”Fraglos wußte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daß den Juden, die in der Regel in aller Öffentlichkeit zur Deportation zusammengetrieben wurden, ein schlimmes Schicksal bevorstand”, p.16.
[43] 同注3,蒙森序,”Das NS-Regime beruhte geradezu auf dem eingeübten Mechanismus kollektiver Verdrängung unbequemer oder verhängnisvoller Einsichten. … Auch Adolf Eichmann ist ein klassisches Beispiel für den Mechanismus, der subsidiäre Tugenden zur Rechtfertigung von Mord instrumentalisierte”, p.17.
[44] 同注3,蒙森序,”Dazu trat eine lange vor 1933 anzutreffende moralische Indifferenz der Mitglieder der Funktionselite”, p.17.
[45] 同注3,蒙森序,”Dies hing zutiefst mit dem Problem der deutsch-jüdischen Identität zusammen”, p35,
“Das Studium der Philosophie in Marburg und Heidelberg, die nie ganz erloschene Jugendliebe zu Martin Heidegger”, p.35,
“Dies gilt nicht zuletzt für die Spannung zwischen ihrem subjektiv klar empfundenen “Jüdischsein” und ihrer unaufhebbaren Bindung an die durch Idealismus und Romantik nachhaltig geprägte deutsche kulturelle Tradition”, p.36,
“Sie blieb trotz ärmlichster Lebensbedingungen, die sich erst in den 50er Jahren verbesserten, ein Bourgeois bis in die letzten Fasern ihres Wesens”. p.39.
[46] 同注3蒙森序,”Hannah Arendts Interpretation lückenhaft, manchesmal nicht widerspruchsfrei und quellenkritisch nicht hinreichend abgesichert”, p.14.
[47] 同注3蒙森序,Sie blieb ein Kind der deutschen Existenzphilosophie und deren ausgeprägt elitärer und a-politischer Einstellung. … Die Begrenzung ihres theoretischen Werks auf die politische Philosophie im engeren Sinn, ganz in der Tradition Montesquieus und der ontologisch interpretierten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tritt in der Ausklammerung der sozialen Frage eindrücklich entgegen, … p.39
[48] 同注3蒙森序,”Die für Hannah Arendt charakteristische Form dialektischen Argumentierens geht auf die intensive Berührung mit der frühen Existenzphilosophie zurück. Der antihistorische Grundzug, der … sondern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allgemein hervorbrach und sich gegen den Wertrelativismus wandte, kennzeichnet auch Hannah Arendts philosophisches und publizistisches CEuvre. So konnte sie aus der Tradition eines positivistischen Spezialistentums ausbrechen und unterschiedlich Epochenerfahrungen, ganz im Anklag an aufklärerisches Denken, intellektuell zusammenzwingen, was ihr faszinierende Einsichten in universelle Strukturen ermöglichte, aber mitunter nicht ohne gewaltsame Konstruktionen abging. Im Grunde hatte sie keine Methode, sondern fügte mit impressionistisch-einfühlender Assoziationskraft unterschiedliche Gegenstände in eine von ontologischen Kategorien geprägte Gesamtsicht zusammen”, p.35.
重读《一九八四》感思
仲维光
五年前,由于当年插队时也走向这条不归路的朋友认为,北岛2009年编辑出版的那本《七十年代》竟然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沉浸在红卫兵时代的革命豪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希望我能够写篇书评。我没有时间撰写,但是突然想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和六十年前,1949年出版的,奥威尔写的《一九八四》做一个对比。因为二者都是以年代为书名,并且都是涉及极权主义社会问题的书。为此,我重读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在1970年代末期,是外文局出版的内部翻译读物。我留下的印象是一本政治小说,尖锐地讽刺了共产党社会的那类专制。由于我觉得自己已经身临其境,没有觉得那体会陌生到哪里去,因此我居然没感到深刻到哪里去。现在,时过三十年,我自己的思想已经彻底地脱去了那个社会给我的桎梏,完成了变化,然而再读《一九八四》,我却真的没料到,这才读出它的真谛。它的深刻,入木三分,甚至可说是刺破星空的远见,无论就思想还是文学性都让我瞠目结舌。
四十七岁就去世的奥威尔让我叹服,惊为天人!他没有和我一样在这样一个极权社会生活过,但是对于极权主义社会对于人性的彻底改变,对于思想结构的彻底扭曲,对于社会及世界秩序的重构,竟然能够如此深刻,且有远见地描述出来。真的只能够说是天才!
天才用感觉和思维就能够洞穿一切,干才用自己的勤奋,在人家的启发下,能够逐渐认识到这些,庸才或者说无才的人,则就是在人家都已经牙白口清地讲明的时候,还是一盆浆糊地在那里喃喃自语。当然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界、精神界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智力问题,还有更让人沮丧的道德问题、质量问题。很多人拒不认识基本的道理和事实,只因为名利,只因为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为虎作伥,以及这个社会中固有的二者的混杂,假作真来真亦假。
其实天才揭示的问题一般都不是复杂的问题,而是基本问题,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到、认识到。而对此,一旦觉悟它经常让人立即产生的反应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没想到。这样的问题近如生活问题、社会问题,远如艰深的物理问题,如量子论、相对论的创生,莫不如此。
我的觉悟可以充分说明这点。因为成年之前,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个世俗的神学教义的教育和禁锢,即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误认为、甚至可说是信仰为是所谓哲学和学术,而在走向成年,有了一些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我有了不断追问的能力、思维能力,就逐渐解脱了它们,步入正途,或者说回到了人类正常追求的道路,我对此的体会真的是太深了,在稍后闲暇的时候,我一定会写文章专门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问题既不是哲学问题,也不是学术问题”。
它真的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专制思想,在最基本的人的感觉和思想上都是禁不住追问和推敲的。我作为一个完全是在共产党蒙蔽教育下的中学生,只因为有了阅读、认字的能力,就能从缝隙中逐渐摸索到这一切。这一点前辈知识分子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证明。
奥威尔只经历了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二次大战,就能够从外面从根本上、入木三分地揭示它、预言它。弗格林和波普则作为高中毕业生,只在短暂的被它迷惑了几个月后就看到,在知识领域,马克思是个骗子,因为他把怀有个人政治目的的“观念论”,一个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拿到知识和精神领域,作为“知识”和“精神”的替代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来误导并且左右民众,而由此,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论,这种世俗化的神学就一定导致极权主义专制。所以,阿隆才语重心长地说出: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笔者根据《阿隆回忆录》英文本,468页,德文本,483页,订正了中文本922页的译文)
而就为此,我在谈到大陆的一些知识精英,就是在遭受到残酷的整肃的时候,依然沉迷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我认为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知识”和“精神”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一般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意识形态化的人,政治化、党派化了的人。
在我过去半生对于共产党文化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就为此,在2013年重读《一九八四》的时候,我深感惭愧,我已经比只有四十七岁寿命的奥威尔活的更长,可我还是没有达到他的深度和高度。为此,在这第二次阅读中,我几乎是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重读了《一九八四》,尤其是这本书的附录,那些个对于双重思想、双重人格,对于再造语言和思维,让人们忘记历史和传统,让人们忘记自己正常的人性的《真理部》的存在的描述,每一个字都打在了我灵魂深处,思想深处。为了准确立即,我甚至只好找来英文原文及德文本。为此,和北岛们不同,回顾1970年代末期,我深感惭愧,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自以为已经从哪个社会中反叛,并且走出很远的距离的时候,居然还是远远没有读懂奥威尔,如果我那时读懂了奥威尔,那么我后来的文字就会更迅速地走向成熟。
就为此,北岛编辑的《七十年代》就不用评述了,因为它甚至没有感到极权主义的恶臭,没有感到六十年前,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揭示的氛围,更没有厌恶和反省,当然更没有感到我们这代人身上显示出来的活生生的“变形记”。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这两三代人都是真理部的后代,任何人都能够、也应该感到,你说的话,你唱的歌,你呵出的气,你的知识结构都是这个真理部给你的。如果你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感到这些,改变这些,就是出国留学了,所谓反共了,也依然如此,依然是侏儒……你呵出的还是红卫兵时代的气,还是真理部灌输给你的所谓历史感、所谓革命气息、所谓学术。
为此,奥威尔的文字、阿隆的论断对我们来说是一面镜子,一把准尺,而你如果不但不想对着它照照自己、反省自己,反而想回避它、涂抹自己,那就双倍地证明了你要么智力出了问题,要么道德出了问题。
当然2013年的这次阅读给我的不仅是对以往的反省,它还给了我更为深远的启示。
《一九八四》,奥威尔的深刻之处还远不在1984,而是在他对此后的五十年的预言和设想,即《一九八四》绝对不仅是对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社会的认识。
奥威尔不只是反对共产党专制,而是更广泛,更根本的对于人类在二十世纪不断发生的灾难、人类未来的关注,对于现代化,即所谓西化的根本性问题的思索和担心。在这个意义上,他,以及波普、阿隆等思想家之所以对共产党问题如此深究,其实也都是出于这个根本的对于人类未来的关心。
一次世界性的战争、一个专制甚至几个专制国家乃至集团,人们可能在对抗中取得胜利,可是它是否会反复出现,是否会不断地让几千万人付出生命,是否不断有人会公然用枪炮在东柏林、在布达佩斯、在拉萨、在布拉格,在北京的街头和广场屠杀民众?——它是否会成为一种趋势,威胁到人类的未来,威胁到人类的存在根本?这才是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最根本的关切。
西方政教分离,近代化以后带来的问题已经困扰这个世界一百多年了。不仅是因为他们带来了两个极权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带来永远不断的各种类型的族群问题、信仰问题、文化问题的对抗,乃至征战、屠杀,带来自由经济名义下的毫无道德的勾结和扩张,而且还因为在他们自己的身体中也已经渗透了这类问题,渗透了不断蘖生这些病毒的病原。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担心的已经不只是东亚国和欧亚国,而是大洋国问题。他感到,最危险的未来是:英国和美国的发展走向!大洋国的孤立主义、实用主义、对人的统治监视手段,对人性的蔑视,大洋国为了权力的彻底的物质主义,也就是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对称的、又一个西方文化中的彻底的的物质主义——即唯物主义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今天最大的危险。在面对2017年的世界现实的时候,阅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让你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此时在何处!
在奥威尔去世六十六年后,难道我们正在从另外一个侧面复制1930年代,重新面对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百年前,由于政治和经济危机,欧洲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各类意识形态及其以它为武器的党团风起、保守主义风起,民族主义风起,基督教教会救世说风起……。在这样的飓风中,欧洲曾经从1919年几十个民主国家到1940年只剩下五个民主国家,百年后,现在,我们再次由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及难民问题重新陷于动荡的浪涛中。毫无疑问,孤立主义、白人优先、基督教优先、文化优越主义是民主的死敌,是世界动乱和灾难的根源。如果人们现在任其泛滥,不断任其随意地碰撞价值底线,民主制度及这个世界肯定会走向又一次危机!
现代化走向,西方近代带来的价值及文明能够解救自己,走出这个悖谬境地吗?至少眼下的答案还不能够肯定地说能。为此,在这个意义上,在已经远远超过直接的反对极权主义的意义上,即在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会不断产生类似的威胁的意义上,我推荐有思想、有感觉的人重新阅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没了《一九八四》一书更广阔地对根本的价值问题关怀和思想基础的反共,将会再次成为党同伐异、政治性、工具性的反共,唯有政治的反共不过是饮鸩止渴,因为希特勒也曾进攻过苏联,可它没有为世界带来和平及幸福,更何况希特勒首先是和苏联签订了合约。
人类有着不可触犯的底线和自己的尊严。那就是任何人、任何族群、任何文化都是平权的。和谐幸福的生活需要开放,而不是封闭!人类需要任何人都不得碰撞、亵渎的伦理!
2017.1.27,德国·埃森
专访德国汉学家蒋永学(上):为什么会编辑出版台湾戒严问题文学选集

漢學家蔣永學
德文本纪念台湾解严三十周年台湾文学选集的出版,二〇一七年在欧洲出版界和学界都肯定是一个重要事件。为此记者对该书的编译者,汉学家蒋永学先生做了专访。
二〇一七年是台湾宣布解严三十周年。这对华人世界,对亚洲的社会和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期。因为“戒严”和“解严”不仅关系到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可以说“间接”促发了中国大陆民众对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质疑及八九年的事件,“直接”使得在八九年后在大陆陷于全世界的制裁时,力图摆脱孤立、积极发展经济时,借助台湾的资本成为可能。从而拯救了八九年后大陆共产党政府的孤立,以及没有在世界的制裁下经济萎缩。
毫无疑问,“戒严”和“解严”三十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研究的历史性事件,但是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最早在出版界、学界涉及纪念解严三十周年的却是在德国。汉学家蒋永学先生在进入二〇一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就在德国出版了关于台湾解严三十年的纪念文学选集,《戒严——台湾文学选集》。
一位学者对记者说,这本书不仅卷帙相当——四百五十页,选材全面、丰富,而且装帧考究、严肃,他相信,这本书对于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及相关人士,在今后数年中都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参考文献。为此,记者进一步特别采访了这本书的编译者蒋永学先生(Thilo Diefenbach)。
关于他什么时候决定编选这样一本文集,蒋永学先生对记者说:“我大概三四年前就决定要编辑一本台湾短篇小说集,当时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选择什么题目作为重点。因为台湾的文学非常丰富,不只是在题材上,而且在数量都非常丰富,比如说,只是在二〇一二年大概就有四千多篇短篇小说问世,谁也看不完,那么如何能够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呢?”
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他介绍说:“为此我想,代表性可能不是最合适的选在标准,因为每个文学研究者对于某个作家,或者某个作品的代表性都会有自己看法,为此我最后想到,二〇一七年是解严三十周年,我想我可以借此机会搜集一些跟解严前后,跟台湾民主化有关的文学作品和故事,但是还是有些担心,如果只是这样,书的内容可能还是有些单调,于是我又加了一些不太有政治性的小说,并且请了另外几位汉学家为这本书提供了不同内容的作品。”
对于台湾文学及戒严和解严问题在德国出版界、学界的情况,蒋永学先生说:“就我所知,关于台湾戒严时期的德文作品非常少。德文的台湾的短篇小说集有过两本。第一本是一九八二年问世,第二本是一九八六年出版。为此我们能看出来,这两本书都是在解严之前出版的,已经不能够反映现在台湾的社会和文学情况,而且反映的是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再说两本的视角都比较狭窄,第一本书翻译的基本上都是本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第二本重点是外省作家的作品。这个现象当然和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直接的关系。两本书当然到现在依然很有价值,读起来很有意思,只是它们无法让德国人了解解严以后的、现在的台湾。”
关于这本书所选内容,他介绍说,“所以我来编辑这本书,尽力介绍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的不同方面、不同作家,里面有老的、有少的,男的、女的,偏蓝的、偏绿的,很有名的,不太有名的,本省人、外省人、汉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有。”
为此关于内容,他进一步介绍说,“其实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以前那两本书完全忽视了原住民作家。题材,这本书中选的作品大多数是短篇小说,也有一些散文,有一些是用幽默描写台湾戒严时代的现象,也有一些写的非常悲观、非常黑暗。但是在我的书里第二种是比较少数的。”
在这篇采访的(下),蒋永学先生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谈了他为什么、以及如何编辑了这本书。
(特约记者:天溢 )
自由亞洲電台/2017/1/27
汉学家蒋永学先生编译出版的《戒严——台湾文学选集》介绍了在另外一个中文社会中,另外一种文学及华人的情况。

德文版《戒严——台湾文学选集》的新书推介——天溢提供
一九八七年,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蒋经国总统宣布,在七月十五日解除已经实施了三十八年五十六天的戒严法。三十年后,二〇一七年新年伊始,德国学者蒋永学(Thilo Diefenbach)在德国推出了纪念解严三十年,有关戒严和解严问题的德文本台湾文学选集。这本书以杨逵一九四九年的“和平宣言”开始,按照年代顺序收录了黄春明“两万年的历史”、李乔的“告密者”、李潼的“铜像店韩老爹”、王湘琦的“政治白痴”、李启源的“解严年代的爱情”、刘梓洁的“父后七日”等作品,最后以二〇一六年年胡晴舫的“世界”收尾,总共三十篇文字。
一位了解这个领域的文化问题的学者对记者说,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德国出版界和学界的一个空白,而且在关于文学、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的了解和研究上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为此,记者在对蒋永学先生的采访的第二部分,请他谈了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这本书,蒋永学先生首先说:“我书里的第一篇是杨奎先生一九四九年写的‘和平宣言’,正好是在戒严时期的开端写的,国民党还没有彻底溃败到台湾。而最后一篇虽然是二〇一六年发表的,但是里面也出现戒严这两个字,这表明戒严这个题目到现在对台湾人还有影响,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我的书仔细地介绍了台湾解严前后的时代,德文出版界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介绍作品。”
对于这本书在了解有关中文文学及文化问题上的意义,他说:“中国文学,现在德国翻译过来的大多是非常有名的作家,莫言、苏童等,他们的作品当然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情况,但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两码事,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我的这本书跟中国大陆文学区别应该很大。虽然我不是特别了解中国大陆文学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从内容、可能也从风格、题材上都是很不同的。”
对于戒严、解严、台湾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联系,他说:“我编辑这本书当然也是要把台湾的情况介绍给德国读者,因为我觉得了解台湾情况的德国人、欧洲人很少。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很可惜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不了解台湾的人无法了解中国,也无法了解东亚的情况,无法了解东亚的历史。台湾在东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谁不了解这个角色,谁就无法把握那里的整个局面,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问题,尤其是历史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德国人应该进一步注意台湾的情况,并且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提高德国人对于台湾的注意。”
蒋永学先生说,这本书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德国和台湾朋友的帮助。对此他说:“我想,我必须衷心感谢所有支持这本书的编译过程的人。首先我要感谢所有那些让我翻译他们作品的台湾作家,他们都对我非常友好,都和乐意并且同意了我的请求。国立台湾文学馆的人士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还有四位德国汉学家,包惠夫(Wolf Baus)、毕鲁直(Lutz Bieg)、何致瀚(Hans Peter Hoffmann)、马嘉琳(Katharina Markgraf),他们提供了他们所翻译的和编辑的资料。最后我还要感谢很多台湾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其它方面帮助和支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台湾书法家江柏萱,她为我书写了书的封面的书法。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我的计划无法实现。”
(特约记者:天溢)
自由亚洲电台/2017/1/30
来源:艾鸽文学艺术网
冤声咽。一纸判令音容绝。
音容绝。
九泉之下,杜鹃啼血。
人寰乐极新佳节。冤魂依旧空悲切。
空悲切。
真凶不言,永无日月。
注:21岁青年聂树斌被冤判死刑,高院核准死刑并执行。22年后真凶自首,最高院方撤销原案恢复名誉。
天气预报说,加拿大的这个冬天将会漫长而酷寒。我从温暖的澳大利亚回到多伦多已经是11月下旬,雪还没有下,但我内心很静,很定。
诗友江南和朋友来访,不仅带来了南方的暖意,还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任社长的《北美乌鸦诗社》,将首届乌鸦诗歌奖颁发给我。在这个诗性严重缺失的时代,在这个血腥染满眼睛的时代,在这个审美能力遭废弃的时代,在这个暴力统一了情感的时代,感谢江南先生和《北美乌鸦诗社》,在酷寒袭来之前,送来了安慰和温暖。
我的诗歌创作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那时还没有机会读到什么好诗。这些年,虽然生活忙碌,世事变迁,但一直有诗歌相伴。江南先生问我:“是否写诗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说:“不,写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雪魂飘隐处 满目尽葱茏》中介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写诗的心境和情境:“诗歌那时是我暗淡无光的生活中一盏暖暖的灯,是我寂寞无趣的日子里一个秘密花园,是我孤独无依的旅程上一排环翔的信鸽。诗歌是我的密友、谈伴、情感的依靠。诗歌是我真情的宫殿,挚诚的楼阁”。时间的洪流洗礼和侵漫了人生的大部分领域,但情怀不改,诗性仍在,我总会在一些陡然怔忡的时刻兀自感慨。
我,是幸运的!我的诗,是幸运的!
近三十年,关注人权、从事民运、人道声援、游说请愿、举办会议、演讲座谈、坚持写作、抨击共产、新闻采访、专栏评论、紧急救助、街头呐喊,支持蒙维藏,关怀良心犯……,我一路疾行,无暇他顾,更疏于与人联络情感,没能向那些天涯海角或近在身边的我诗歌的共鸣者致谢。在此我一并鞠躬感恩。
2006年,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刘真大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我的诗,非常喜欢。后经黄河清兄穿针引线,我们开始电邮交往。她得知我想在国内出诗集,于是不辞辛苦到处奔波替我找出版社。一个出版社看了我的诗稿之后,决定拿下一个预定的出版计划,出版我的诗集。但是到了国家出版总署这一关,立即遭到拦截,出版社也遭到责难。我的诗集没有能够出版,中共公安、文化、出版三部委仍然聯合发布文件在全国查堵。
刘真大姐在《<觅雪魂>的另一种荣幸》中写道:“在一个无诗的时代,《觅雪魂》能够脱颖而出,可谓当今诗坛的一大幸事,而且在所有的诗集都面临默默无闻的命运时,这本《觅雪魂》却受到了国内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查堵,国内大小媒体,无一遗漏地传达了文件通知,严禁出版、发表或转发盛雪的《觅雪魂》,盛雪及《觅雪魂》一下被国内所有传媒人所知晓,这本还未出版就遭禁的《觅雪魂》,凭藉这种力量,迅速地走遍了祖国大地,而且成了许多人关注或寻觅的对象。这种客观的效应,不能不是《觅雪魂》的另一种荣幸!”
我1989年8月抵达加拿大,自此走入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行列;自此,我的绝大多数时间、精力、智慧、思考、金钱、行动、人脉,也都投入到了这场事业。我的诗歌创作成为在机场、车站、会议间隙、无奈等候等寂寥一刻,心绪不期然的飞扬。
诗歌写得少了,好在总有些非写不可时刻。我的诗是幸运的,获得了令人潸然泪下的共鸣。智慧而美丽的女作家北明在《丢失后的残字》中写道:“就是这些诗,在每一个平庸的日子,每一个平凡时分,收集着散失的文明碎片,连接着隔绝的村落,表述着我们内心的独白,抚慰每一个孤独的灵魂。也是这些在心灵的荒郊野外飘荡的残字,在白天和黑夜,在流亡途中,在异国他乡,记录着我们个人和民族的苦难,坚守着我们的人性,让不幸受难的生命在我们的怀念中复活,从而使阳光君临我们内心和这个社会。千年暗室,一灯可明。这是盛雪这本诗集的功能。”
被誉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先生在《推薦盛雪詩集<覓雪魂>》中,从一个民运同道的视角解读了我的独白:“作為知名的民運人士,盛雪也遭受過很多誤解乃至惡意的攻擊和誹謗,但她能不動聲色,淡然處之。然而正如她一首小詩所說:”只是能夠承受打擊/並不是感受不到傷害”,此所謂堅強。此等堅強,令人肅然起敬。”
2008年3月在香港的诗集发布会上遇到作家盛慧。这位外表文秀恬淡,略显腼腆的年轻人告别后,居然写出一篇《盛雪诗歌的兵器谱》。读着这独特而传神的诗评,我禁不住大声笑起来:“说实话,我虽然习诗多年,但对于当下的诗歌是极不满意的,很多诗人像巫师,对于他们来说,写诗就像念咒语,语言像是花拳绣腿,虽然极尽华丽,但读完之后,却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盛雪的诗,却迵然不同,她让我感到了久违的痛快淋漓。读完诗集,我耳边回绕的竟是清脆的兵器之声,我深知,对于一个自由的骑士和民主的斗士来说,诗歌就是她手中的兵器,在我看来,她最得心应手的是:飞镖、快刀、断魂枪和流星锤这四样兵器。”
不少朋友说,在陈奎德为我的诗集写序之后,为我的诗写评介是困难的:“恍如在古老诗国的上空,黑森森的天穹下,我看见了一片洁白雪花,正在熊熊燃烧。红裹挟着白,闪烁在无边的黑幕中。那就是诗,盛雪的诗,以红、黑、白三色为主调的诗。以古韵和今语连缀的新诗,在诗歌衰微的时代,她倔犟地出场,身披浸透二十世纪血泪的三色衫,上承古贤,下开新篇,百折不回,寻觅雪魂,复兴诗心。‘虽千万人,吾往矣’”。 是的,陈奎德先生洞悉古今的穿透力和俯瞰苍生的大慈悲,汇聚成文字,流泄于笔端,我只有默默顶礼。
江南先生介绍说,诗社之所以取名“乌鸦”,是有感于乌鸦是自然界中一种向死而生、反哺报恩、特立独行的禽鸟。诗社以此立意,寄望于,诗人既有追求自由,热爱真理,敢于抗拒暴政恩典的勇气;也有怀德感恩,心存大爱,拥有不惧孤独苦难的秉性。
感谢还有江南先生这样的诗人,有北美乌鸦诗社这个的处所,还有一批狂妄着理想狂妄着太阳的追梦人。
我深知,我们正处在一个向死而生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悲壮而倔犟的出场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2016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