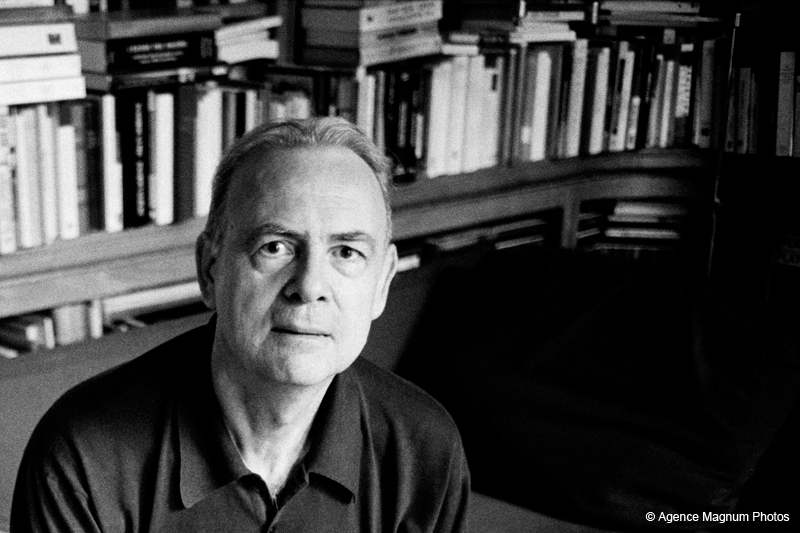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姜广平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这个可怜的男人,在文学世界里挣扎得太辛苦了,完全没有了在军政界那种万人瞩目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人”的风度。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870——1953。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以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无论这种认真是出于哪一种目的。我们也没有必象如果这两位作家真的回国会有什么样的情形等着他们。
斯大林的文学情怀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并不像国内某些学者所谓斯大林是一个被判了文学死刑同时也判处文学以死刑的人。应该看到,由于他的另一种身份,他的文学情怀遭到了扭曲,他的文学良知与文学人格也丧失殆尽并进而使文学蒙难缪斯蒙羞。这不能不认为是斯大林的人生悲剧和俄罗斯的悲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极权专政的状态之下,俄罗斯的文学仍然发育得让世人吃惊。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他对文学的论述,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无法达到马恩的高度,超过列宁同志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二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4年(1893年─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但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虽然他从未指望过得到诗坛的承认,却在初出茅庐之时即得到普遍的认可。格鲁吉亚的许多刊物一度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格鲁吉亚的青年诗人提供版面,他的诗句在读者中争相传诵。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1837─1907)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是无庸置疑的,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70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不难猜出,这道命令来自何人。就这样,根据领袖斯大林的旨意,诗人斯大林未能成为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 当然,如果斯大林获得了斯大林奖金,那么,这种游戏便实在太低级了。这种幼稚甚至显得可笑的游戏显然是斯大林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的高贵。高贵与高尚是大不相同的。高贵是一种更能切入人的心灵与灵魂的品质,高尚则只是这种品质的简单而没有血肉的道德描述。事实上,高尚也不足以描述高贵的全部。这里让我们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青年斯大林改变志向投身革命并在之后始终闭口不言“当年事”?柯秋科夫这样解释:“19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做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①
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来自斯大林本人关于告别诗坛的解释。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诗歌的经历。但是,在我们看来,贵为泱泱大国领袖的斯大林一生太过辉煌,要记述的实在太多太多,这样的诗歌经历与斯大林的政治经历相比确实不值一提,如果与像叶赛宁、蒲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相比,更不值一提,如果再抬出更早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这点诗歌成绩简直不值一哂。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正因为他看到了诗歌的高贵而放弃了诗歌。当然,无法理解的是,当他的政治理想终于获得实现,为什么又对诗人举起了屠刀?
可能,在斯大林的心中,他不愿让诗歌撼到他的政治,绝不容许!或者,这个时候的斯大林,早已经认识到作为政治家与军事领袖,是不需要诗歌的。诗歌只能让政治与军事变得软弱无力,而政治与军事都需要暴力的支撑。在斯大林看来,也许,在执掌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之后,从意识形态上看,对诗歌的贵族气与布尔乔亚气质,必须认真地矫正。
而另一方面,要斯大林认输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有榜样在前,斯大林肯定要像他的前辈如马恩与列宁那样对文学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指点与评论。斯大林既不肯轻易地在前辈们面前认输,也同样不愿意在诗人与评论家面前认输。
客观上说,斯大林的语言学与文学造诣显然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譬如说语言学方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的修为达到了一个语言学家的高度。在与巴赫金较量时,我们是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的。
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赫金与斯大林扭结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加强对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统治,这种集权思潮波及到论述宗教、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参与A·A·梅耶组织的“复活小组”受到牵连,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后于1936年刑满释放。这件事似乎与斯大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巴赫金在50年代斯大林语言论问世之后,曾被要求在公众场合发表他对斯大林语言论的看法。而50年代,是巴赫金话语类型论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众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统治苏维埃语言学达二十年之久(1930年—1950年)的“马尔学派”神话,因《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论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破灭。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这种反响在斯大林去世后,仍然持续。这之前,任职于摩尔多瓦师范大学的巴赫金因公务需要,被要求提交关于论述《在I·V·斯大林论述的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这一学说基础上的对话性话语的问题》的报告,50年代初,巴赫金余兴未了,又撰写了《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的正文和相关的笔记存稿中,有巴赫金对斯大林论文中的有关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时还选取了论述斯大林论文的其他论文中的间接引用部分。有了这样的前提,巴赫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的。
从这一点看,至少斯大林在语言学上的论述是与巴赫金有着某种“同声期”的。②
当然,就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因为,在《巴赫金著作全集》出版之时,编者们出于对死者遗愿的尊重,将其中的“低级、庸俗”和“个人崇拜的痕迹”删除了。但是,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删除,毕竟,巴赫金的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即使删除了某些痕迹,仍然还零星地分布着斯大林论文里的东西。
《言语体裁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结构上采取了对年轻的语言学者提出的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的一问一答的形式。这里面的第三问是:“语言的固有特征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没有脱离索绪尔的结构框架。虽然他没有使用索绪尔的术语,但回答的基本结构是前半部分是共时论,后半部分为通时论。
巴赫金与斯大林的对立主要见于巴赫金在准备《言语体裁问题》时写的笔记《预备资料》中。这里面直接指出了“斯大林关于语言的思考方法是把语言作为体系(语言本身就是规范体系)考察的思考方法”,而巴赫金则关心“语言交际”的过程。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对立,在巴赫金并不是一种突然的选择,这种对立、对比,是巴赫金小组20年代后期彻底考虑后的立场。
应该看到,巴赫金毫不隐瞒地表明是以斯大林语言论作为前提的。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这样看:巴赫金承袭了斯大林(索绪尔)的立场,没有改变语言体系结构的基本方向。但是,在语言体系结构的尝试方面,巴赫金采取了与斯大林对立的态度,一直坚持自己补充完整的“言语——对话论”。但应该看到,巴赫金这部没有最终完成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其对话对手并不是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
在对待巴赫金的问题上,斯大林所采取的立场与态度都是相当不错的,斯大林在这里显得相当儒雅,有一种学者气派。这可能是因为巴赫金仅仅作为一个学者出现,在深层问题上,不可能像作家与诗人一样可以撼动着根基性或意识形态的东西。然而,除了学术立场以外,巴赫金对斯大林基本上是全面否定的。
这显然是与斯大林对文学的摧残紧密相关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左琴科。
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曾有一篇《列宁和哨兵》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然而就是这篇文章给左琴科带来了麻烦。左琴科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最初他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但左琴科担心捷尔任斯基认为是影射他,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斯大林便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事隔多年,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日丹诺夫的这篇报告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③
我们知道,就是这位日丹诺夫,后来掌控了全苏的意识形态。
但另一角度看这则材料,未尝不表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关注甚深。
成了领袖以后的斯大林,诗才方面肯定日渐枯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仍然无法忘情于诗歌,甚到不惜以一种斗法的手段与真正的诗人们进行过一次暗中交手。但是,这次交手,既不是太光彩,其行为也再不像年轻诗人斯大林的诗那么为人所追捧了。
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这位“朋友”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干得很出色,他操持着一个大国,对所有人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诗歌的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
当然,强行攫取这个权柄也很简单。在历史上,秦始皇时代、希特勒时代以及“文革”时代都采取过同样简单而又有效的手段。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一次否决权。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冒着失去生存的权利的危险。这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个帕斯捷尔纳克大相径庭,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确实令人感奋。
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的国度里宣判了斯大林的死刑,而斯大林却有权在现实的国度里宣判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及其诗歌的死刑。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苏维埃制度。于是全苏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但幸运的是,其时已经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被愚弄了的苏维埃公民愤怒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要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但诗人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从此,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③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他的第一本自传《安全证书》中找到一些答案呢?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局限于年轻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艺术中。在他与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中,他一方面强调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影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与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小团体决裂的必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整个30年代不断地被印售,虽然文化部门对他作品中的“个人倾向”、“形式主义”和“自我纵容”越来越不满。1934年,斯大林为加强中央政府同艺术家的联系,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宣布了官方的美学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协会要求作家接近社会,根据党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描绘苏维埃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顺从此原则,1937年他移居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居住地,这是他与莫斯科现代艺术相脱离的象征。
而这在当时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是对马雅可夫斯基采取这样的态度也都是非常危险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特别喜欢的诗人。斯大林曾经这样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托洛斯基所钟爱的诗人。
当然,应该看到,无论左琴科多么伟大,但他与斯大林的交锋,其层面与意义都不甚巨大,他无法与在诗国里判处斯大林死刑的帕斯捷尔纳克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帕斯捷尔纳克毕其一生极力靠拢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生活中却对当局逆来顺受;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当局的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也即是在1960年5月30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另一个作家,但却从反面体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扼杀。
这个人就是康·米·西蒙诺夫。他是苏联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生于1915年11月28日,卒于1979年8月28日。1938年他在高尔基文学院毕业后投身文学创作,成名作是头一个剧本《我城一少年》。后来,他又创作了表现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俄罗斯人》。1943—1944年西蒙诺夫完成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此外,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50年代后西蒙诺夫致力于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代表作为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第一部《生者与死者》,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后的夏天》)。西蒙诺夫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批新人。他从一个工人成长为苏联著名的作家,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他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出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主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都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
西蒙诺夫在当时苏联文坛真可谓红极一时。这样一个才华全面的作家可惜就这样成了政治的侏儒。他太善于揣摩斯大林的心理了,他用作品完美地图解了斯大林的政策。他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组织作家围攻佐琴科,充当了文坛的打手。斯大林死后,他还写了《我们的责任》,说要完成斯大林的遗愿。赫鲁晓夫看后大怒,把他撤职了。
西蒙诺夫的作品,其实正是米兰·昆德拉所讲的那种“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它们不可能以一种思考式的探询作为它的质地。“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之论见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如果我们要诠释西蒙诺夫的作品,完全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来表示,那就是,它所要展现的,不可能是善与恶之间的人性的较量,而是一些善与最善之间的小把戏。这就是苏联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如果不遵从这样的艺术原则,谁就将是斯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的敌人。这样的敌人,到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大体上有: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
西蒙诺夫不在其列,于是,西蒙诺夫的文学便是一种死的文学,它们喻示了斯大林时代的真正的小说之死或文学之死。而这种死,又是那么残酷!这种残酷是在审查、禁止、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实现的。从品质上讲,这样的作品是以一种死的形态出现的。因为,优秀的作品,其存在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是“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④。西蒙诺夫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包括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很多作品,其文学品质都是极其低劣的。就遑论名气与文学地位低于这两位的那些作家了。
一个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这种状态下体制下的文学,便始终无法达到文学精神的高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蒙诺夫的全部文学价值,可能只存在于他最后那部回忆录——《知情者的见证》(也译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作为一个作家,西蒙诺夫有着善于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和勤于笔记的习惯,这部回忆录的主要部分都是出于他当时所做的详细笔记,这保证了资料的翔实性,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非常生动,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书中也写到了他对斯大林的文学感觉:斯大林读过很多当代苏联文学作品,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从1946年开始,他有机会多次与斯大林接触,主要是参加政治局讨论授与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他感觉到斯大林有时是态度温和、通情达理的,有时又极其严厉、独断专行。
斯大林的这种文学情结的形成也许与俄罗斯作家们的政治态度极为相关。
很多作家是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不与其合作的。这些作家大多在十月革命前就成名了,而且都是些大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国外。1922年托洛斯基下令把包括一些作家在内的学者约1000人用船遣送出国,这条船被称为“哲学家之船”。这些人中,库普林、吉比乌斯、台菲等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重要作家布宁则于1920年红军快到敖德萨时与白军逃到国外了。
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并不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后,他们大多数留了下来。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人。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日丹诺夫骂为“婊子”,受尽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为写《日瓦戈医生》饱受打击与迫害。布尔加可夫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1940年不到50岁就死去,很多作品当时未得发表,大部分作品是在1987年以后重见天日的。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心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表示拥护。这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但并不受政权的重视,也没受到重大打击。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等。
与斯大林走得非常近的作家大多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在苏联文坛出尽了风头。如法捷耶夫,他是苏联作协负责人;前面提到的西蒙诺夫多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考涅楚克,他是话剧《前线》的作者,还担任过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除了上文提及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外,我们再看一看索尔仁尼琴吧。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服过兵役、受过嘉奖。卫国战争入伍,两次获得勋章,大尉军衔。他经常在与挚友的通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信被克格勃检查发现有对斯大林不敬之词,在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被抓了起来,在狱中关了8年。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再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20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扳了一次手腕,在作家当中,肖洛霍夫比较幸运,就像那年他去打猎时,竟然在打到一只野鸡的时候也打下了一个诺贝尔奖一样。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万百人横尸遍野。斯大林政府却“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2.6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5.5万人受审,2110人被枪决”。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⑤
然而这位在政治上“无知”的作家,显然命运好过了其他作家。斯大林就这样放过了他,这倒是令人费解的。
注释:
①《诗人斯大林》:郑体武《译文》2002年第二期
②《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日)北冈诚司著,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③《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迫害引出斯大林接班人之争》:龙飞《天津日报》2004年4月19日
④《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⑤《古怪一族》:陈世旭《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jpg)